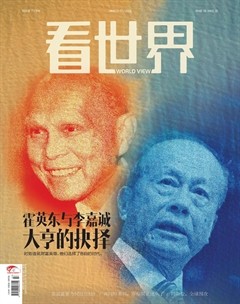15岁的周诗,很想上高中。
2024年中考,朋友都去了高中,可她只考上一所中职学校,从此不再是一路人了。高中的朋友们,过得“很充实”,身在中职,自己则有些“虚无”。课余时间里,她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就跟同学一起打游戏、打牌。
为了进入普高,她想过很多办法。
她提出想休学一年再参加中考,可父母不同意。辗转之下,2025年2月,她在一个中考复读机构学了十几天,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进度。中考报名在即,周诗放弃了,准备留出更多时间复习,等到2026年再参考。
“不想那么早被分流。”周诗并不擅长所有学科,她想,如果进入高中以后再分流,她是不是能选择自己擅长的科目参加考试,也许就能够留在普高?
推迟普职分流,多次成为两会期间的热门话题。
2025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李杨接受采访时提到,建议将分流时间从中考后适当推迟到高中阶段初期,让学生在高中接受一段时间的综合教育后,再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和学业成绩等进行更科学合理的分流。2024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陈众议则呼吁,以十二年义务教育代替九年制义务教育,将“普职分流”推迟到高考阶段。
长期以来,普职分流成为学生、家长的焦虑来源之一。而所谓“推迟分流时间”,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焦虑?“分流焦虑”背后,真正应该直面的问题是什么?
行走在分数线上
刘思知道,自己的儿子要考上高中比较费劲。儿子现在正是初三,在全年级的700多人里排第500名。
儿子已经在学习上花了很多时间。现在初三,儿子一周的时间几乎被学习占满,周末两天,他也要补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四门课,还要抽时间练体育。
“他连洗澡、绞头(剪头发)的时间都没有,”刘思说,“我们不是在正常上课,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
刘思能看出来,儿子对学习不感兴趣。上一对一的补习课,他和老师单独在一个隔间学习,他不听老师讲,而是把脸贴到隔间玻璃上。到了初二去上小班课,他可以花很长时间抠墙皮。最让刘思不能接受的是,儿子会撒谎,说老师没留作业。有一次考试数学得了20分,他告诉刘思,这20分还是他抄来的。
彭莉的女儿也不爱学习。从小学开始,彭莉就会辅导女儿学习,女儿也会听从妈妈的安排,每学期开学前预习功课、做好练习题、自己看网课。但她对待学习并不主动。
而只是按求完成任务,要应对考试是不够的。彭莉告诉笔者,在湖北武汉,学生考试的内容往往比课本上单一的知识点要难很多,学生需要自己肯动脑钻研。上了初中,彭莉不再严格地督促女儿,她的成绩因此持续下滑,入学时她排在区400名,到了初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她掉到了2200名。
刘思和彭莉都估计,以孩子现在的成绩,差不多能上当地的三类高中。再往下掉,就是中职学校。临近中考,学生与家长就像是行走在分数线上,因担忧下坠而紧绷。
因为学习,家庭关系也随之变得紧张。刘思发现,上了初三,有手机的同学变多了,儿子也因为特别想要手机经常和父母吵架。他以自己没有手机为由,不去参加初中的最后一次运动会,因为同学们到时候都可以拿手机玩,就他没有。爸爸原本就有高血压,有一次甚至被儿子气得瘫倒在地上,吃了速效救心丸才好过来。
紧张感背后,是初中生家长对送孩子上普高的执念。

刘思感觉到,在家长中间,焦虑不论成绩。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能排进前50名,家长也担心他中考会发挥失常;“差的更焦虑了”。不少熟识的家长常常来问刘思,未来怎么打算?有一个家长告诉她,他们准备让孩子挂靠上普高,或者是走艺术类,通过画画的特长上一个三类高中。而这意味着高中三年,家庭要支付大约30万。
刘思自己都像是抑郁了。因为要陪着儿子上补习班,还得不停安抚老师,她耗费了太多精力。她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想干,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