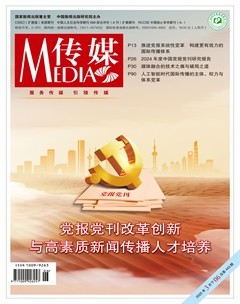摘要:宋代是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书籍在宋代也成为真实意义上的印刷媒介,实现了大众传播模式。作为一种新型传播类型,书籍的数量、出版传播效率均有重大革新,特别是魏晋小说《世说新语》,从“钞本时代”迈向“印本时代”,打破了以往的传播时空局限。经典书籍的印刷出版,产生三重重要的社会影响:在经济维度,书商加速书籍生产并带动域外贸易;在文化维度,印刷物扩充文学阅读群体,扩大文人交游圈,并使学术研讨成为可能;在政治维度,出版活动有助于强化中央集权、塑造社会风气、优化人才选拔机制等。
关键词:宋代出版物 《世说新语》 印刷出版物 雕版印刷
在宋代印刷出版《世说新语》等经典书籍的过程中,印刷技术作为“加速器”,促进了信息的广泛流通,使得印刷出版物在经济、文化、政治三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钞本与印本的兴替,为出版物在制定出版发行策略时提供了历史借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印刷物在出版发行过程中所经历的市场刺激、文学拓展、政治治理三条实践路径,有助于启发现代出版业开拓出自身的多元化社会效应。
一、经济维度:印刷出版物“行世”的经济价值探析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代社会积累了大量可用于制作纸张的原材料,如麻、丝等,这为印刷业的发展奠定了材料基础。同时,科举制度盛行和读书风气普及,使得印刷书籍需求量激增,这为印刷出版物的经济价值提供了空间。
1.从钞本到印本的跨时代转型。宋代是印刷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使得宋代出版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书籍种类涵盖历史编纂、儒家经典、医学等,并出版了诗词歌赋合集等满足百姓需求的各类书籍,书籍成为一种可大规模生产流通的商品。在“钞本时代”,由于书籍采用手写方式,书籍的书名、分卷、门数等情况在各本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书籍印刷出版成为难题。进入印刷阶段后,实现了版本的统一和标准化,印本成为认证版本价值的重要手段。
南宋绍兴八年以前,《世说新语》以钞本流传,内容局限、版本芜杂,传播十分受限。绍兴八年,严州知州董弅对《世说新语》进行刊刻,诞生《世说新语》“董本”,“这是为该书首次刻印,此后,《世说新语》进入印本时代”。印本盛行后,钞本渐少,文本面貌趋于统一。“董本”以其清晰稳固的文字呈现,确立了《世说新语》书名与完整体系,成为后续出版的标准模板。后陆游翻刻均以“董本”为蓝本,这进一步扩大了《世说新语》的传播范围。“董本”的行世,揭示出书籍形态的转变价值,为后续规模化印刷提供了先决条件。而宋代正值中国古籍校勘学的繁荣期,不仅官方机构如馆阁、国子监设立了专门的校书部门,地方官员、藏书大家在印本时代到来后,纷纷致力于对前代钞本书籍的校勘,形成了全国上下参与校勘的盛况。
2.官营、坊刻、书院:三元并立的出版生态。印刷术让书籍获取变得相对容易,加之出版商对市场需求的敏锐嗅觉,《世说新语》等大批经典书籍迎来出版盛况,并表现出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中央官刻保障与地方官刻推动。《世说新语》进入“印本时代”后,政府多次组织该书刊刻再版,并通过国子监、崇文院等机构实施“三校”制度,“凡经批准镌刻的书籍,在交付镂版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三校”,此举确保书籍内容的权威与精审。除中央机构以外,宋代地方官刻蔚成风气,南宋印刷业兴盛更是将书籍镌刻版图扩展至全国,在南宋汴京、临安、成都、建阳四大刻书中心,充裕的雕版材料、大量的文人群体与稠密的人口使得书籍需求激增。这些地区书坊众多,文人会集,通过地方官刻系统,《世说新语》等大批书籍在全国范围内加速传播。在中央与地方机构的推动下,大批书籍校勘审定工作得到空前支持。
二是坊刻与私刻书籍更强的商品性。宋代书坊集售书与刻书功能于一体,实为私营商业出版发行机构,遍布各地,印刷量大。随着《世说新语》的印本问世,杭州、苏州、成都等文化重镇成为其出版中心。书坊承接刻印售卖任务,加速了书籍的传播速率,部分书肆主人更集收藏、编纂、印刷、销售于一身,实现了文化创作与商业运作的有机结合。宋咸淳年间明州刻本《佛祖统纪》的“刊板后记”称:“拟办纸印造万部为最初流通。”足见当时书籍出版的盛况,由此可窥探《世说新语》印刷生产效率之高。私刻方面,文学家、出版方行动迅速,书籍常标识以“某家塾”的字样,多由官绅、文士等精准印制,典籍广传,佳作迭出,如《渭南文集》《五经》等,私家出版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