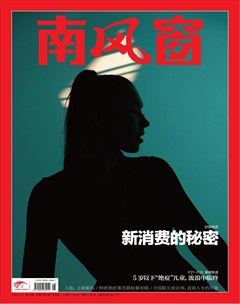2024年9月1日清晨,林秋预感到,她2岁7个月大的儿子即将在家里走向生命的终点。
孩子已经3天没怎么睡觉,熬得眼睛发红。扩散到淋巴的肿瘤挤压着他的气道,导致他呼吸困难,入睡时肌肉放松会加重窒息,因此他每睡着两分钟就会醒来。他一刻也不能离开林秋,一旦找不着了,他就哭着喊妈妈。在那些漫长的夜晚,母子俩睁着眼睛面对彼此,一起熬。
倒计时1小时的时候,孩子开始咳出黑色的血,林秋和丈夫唯一能做的事情,是给他擦拭血迹,这个过程持续了半小时。她看着血氧仪上的数字从100变成70,又骤然下滑到20,继而在30左右浮动,直到那个数字一点点变成0。她庆幸孩子终于从痛苦中脱离。
在孩子生命的末期,林秋最大的愿望是找到一张床位,一张医院里的床位,能让孩子借助医疗手段睡个好觉。但直到最后的那个清晨来临,这个愿望都没能实现。
林秋的境遇不是个例。儿童的生命常常会被抢救到最后一刻,但也有这样的一群家长,他们面对孩子罹患的几乎无法治愈的疾病,不愿意幼儿再遭受继续治疗的痛苦。他们希望停止积极治疗,在医院进行安宁疗护,陪伴孩子善终。
但采访呈现出一个群体性困境,5岁以下儿童的父母如果不把孩子送进PICU(儿童重症监护室),他们将很难再找到专业机构提供后续的医疗服务。有很多孩子滞留家中,在持续的痛苦中逝去。
5岁,是一个分水岭。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世卫组织用以衡量各国公共卫生状况、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儿童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20年底,我国儿童医疗保健水平不断提高,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61‰下降到7.5‰。
但追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意外地造成了5岁以下临终儿童的安宁困境。部分医疗机构因没有条件,或难以承受压力而不愿接收他们,导致林秋和她的孩子被忽视了,与她身处同样境遇中的人们,也被忽视了。
选择
2024年8月,妇儿医院肿瘤科医生只给了林秋两个选择:让孩子进PICU,或者办理出院。
她和丈夫不愿意让孩子进PICU。小孩身上长的是睾丸卵黄肿瘤,肿瘤细胞迅速扩散,在几个月时间里已经脱离了原发病灶,向腹部、肺部和淋巴转移。如果选择手术,首先就可能要把他的睾丸全部切掉,而他的生存概率并不因此而提高。
她的丈夫问医生,不想再继续有创治疗,不让孩子受苦,只想缓解一下痛苦,行不行?对方回答说,这种情况他们是不会收的。“我们只想找一个让孩子接下来的日子舒服一点,即使他要走,也要让他走得好一点的地方。他们也告诉我们可以选择那种小孩安宁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找到。”林秋说。
当时,孩子的肺炎很严重,老是喊痛,脖子的转移瘤已经长得很大,压迫气管导致严重呼吸困难,心率接近200。后来林秋去求了泌尿外科的一位女医生,对方看她的孩子可怜,给他们在老院区找到了一张病床。他们只在里面住了3天,每一天,医生都会来找他们谈话,说孩子随时有去PICU的可能,要求他们尽快出院。
她的丈夫问医生,不想再继续有创治疗,不让孩子受苦,只想缓解一下痛苦,行不行?对方回答说,这种情况他们是不会收的。
进PICU还是出院的选择,曾经被摆在很多跟林秋相似的父母面前,秦方也是其中一员。
秦方的孩子叫郭允泽,在他只有4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严重的肺炎发作,秦方曾同意把孩子送进PICU。无法探视,她守着PICU门口过了3天。直到有天允泽被带出来做检查,秦方看见他的手脚被绑住,插着鼻饲,封住了嘴,“他的眼神在告诉我,他很害怕”。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接受这个选项。
在肺炎反复发作的过程中,秦方换了多家医院不断检查,最终从基因检测结果得知,允泽患有不明原因的先天性肺动脉高压。
秦方带着孩子几乎跑遍了全国求诊,在住满了肺动脉高压孩子的病房里,她见证过许多抢救和死亡,有从出生开始就一直插管治疗的宝宝,插管插了几个月,最终还是救不过来。哪怕是这一领域最权威的医生,都只能让她做好心理准备,说孩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离开。
终于在孩子快一岁的时候,秦方明确了自己的想法。她要放弃给孩子继续治疗,“不要去让允泽受一些更大的痛苦”。
疾病发展到晚期,缠绕着郭允泽的是严重的呼吸困难和剧烈的胸痛。一旦症状发作,他就会不受控制地因痛苦而抽搐和叫喊。
类似的急性疼痛也常见于其他疾病终末期儿童,这是一种叠加在慢性癌痛之上的爆发痛。我曾经在病房里见到过一个得尤文肉瘤的小孩,在半小时里经历了八九次爆发痛。她的黄色皮肤上面覆盖着一层青灰色,疼痛发作的时候眼睛和眉头紧皱成一团,嘴唇泛白,颈动脉剧烈跳动。
在那一时期,郭允泽的治疗已经辗转到了一线城市的儿童医院,秦方最后一次被告知只有两个选择。医生同时暗示她,孩子去PICU可能也挺不过来,她只能带着孩子离开。
在3天连续不断的催促中,林秋和丈夫不得不带着孩子离开医院,他们联系了一辆救护车,把孩子转运到一家高端老年护理院。护理院一周收费8000元,但无法提供止痛药,孩子拉不出尿,也没有尿管可以插,他每天晚上都发烧,护理院只能给他吃美林(小儿常用退烧药),除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有天傍晚,由于小孩已经太久没有排尿,林秋夫妇决定开车带他去医院急诊插尿管。他一直喊痛,不让妈妈抱,但林秋还是强忍着抱住他,坐上了车后座。行驶过程中,林秋听见丈夫说,要不开车撞桥一起死了算了。“他说为什么会这样,连收我孩子的一张病床都没有。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只想孩子舒服一点点而已,没有的,不行的,没有一个方向。”插好尿管,他们又开车把孩子抱回护理院,在路上,林秋第一次看见了丈夫流眼泪。
在护理院没有住满一周,他们再次决定离开。小孩天天要黏着妈妈睡,床只有1米宽,林秋每晚都翻不了身。更何况,他们在这里得不到任何医疗支持,每分每秒都在承受煎熬。他们也曾经找过很多做安宁疗护的机构,但是打电话去问的时候,得到的回复都是说没有床位,或者说只接受老人。
吴玲的女儿小叶子和林秋的儿子是在同一个夏天离开的,两个孩子都不满3岁,都在家里去世。小叶子患有神经母细胞瘤,这是一种被称为“儿童癌王”的疾病。吴玲曾拿着检查报告托人问了协和的医生,也查遍了所有她能找到的相关文献,得知孩子到了这个阶段已无法治愈。
她问儿童医院血液科的医生,院内是否有安宁疗护服务,医生说,没有。后来她在网上搜帖子,发现院内其实有可供安宁的地方,但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去到那里,就是一直在这家医院接受放化疗,最后实在治不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体面离开的机会。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她得到的是一个更加明确的答复:“我们有规定,5岁以下不可以。”她只能带着孩子出院回家。

吴玲说自己几乎打电话询问了全市名义上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所有医疗机构。她得到的是一个更加明确的答复:“我们有规定,5岁以下不可以。”她只能带着孩子出院回家。
回家
从疾病被发现到最终离世,神经母细胞瘤在仅仅一个月之内就带走了小叶子的生命。她的身体状况在短时间内恶化,痛得连手指都动不了,压根无法站立,肿瘤细胞甚至侵入了她的视网膜,导致她逐渐失去视力。
回家不是问题的解法。吴玲需要给孩子镇痛,但是控制癌痛最有效的药物,例如芬太尼透皮贴和吗啡针剂,一般只有住院才能使用。当时,她唯一的指望是,找到可以带出医院的、口服的阿片类药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连能给儿童开阿片类药物的门诊都找不到。
从事安宁疗护工作多年的郭艳汝医生,原本负责的是麻醉科的工作,在国内儿童镇痛领域,她是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
2023年底,曾有一名尤文肉瘤患儿家长求助郭艳汝,请她帮忙在当地给孩子开出口服的吗啡缓释片。家长告诉她,当地肿瘤医院只给14岁以上的患者开药,去儿童医院又开不出吗啡来。
隔着1700公里的距离,郭艳汝在网上帮着找熟人、疏通关系,又托人去帮忙打听,但好几位医生都不给开。“这两天还是先给她吃布洛芬吧,还是能止痛。”那位家长对郭艳汝说。
后来郭艳汝了解到,一些省级儿童医院的阿片类药物年平均消耗量只有两位数。她曾听一位省儿童医院药剂科的工作人员说,该院每年吗啡针剂的使用量为十几支。
郭艳汝不解道:“这家医院的大部分临床科室主要收治儿童血液病和实体瘤。在儿童肿瘤外科和血液肿瘤相关科室,到处都是抱着孩子的家长来预约住院,一床难求。难以想象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在进入晚期阶段后,这些孩子去了哪里?每年十几支的吗啡又如何保障他们的镇痛需求?这中间巨大的镇痛药物缺口又如何解决?”
在多年从医经历里,她已经见到过太多被迫回家,却又开不到镇痛药的晚期儿童。2024年,为了帮助更多这样的孩子,郭艳汝开始在网上开设咨询门诊。通过医生朋友之间的关系网络,确实能找到办法为这些孩子提供帮助,为他们寻找可以合理开到药物的途径,但这件事会给朋友们增添很大工作量,也为他们带去潜在风险。
找药困难重重。吴玲一度在想,如果她动用了所有的能力,都找不到安宁疗护机构,也开不出镇痛药,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痛苦的话,她唯一能为女儿做的事情,是不是就只剩下亲手了结她的生命了?
后期介入帮助吴玲一家的社工福川记得,小叶子死后,孩子奶奶曾经在电话里偷偷告诉她,说托关系找医生帮忙开了3粒吗啡,孩子走了用不上了,希望能把3粒吗啡捐给公益机构。在这样的家庭,这几粒药片是比黄金更可贵的资源。“人家让她丢了,她说我不要,有很多人拿不到。我要保存下来,然后我捐给你,你给需要的人。”她听得很心疼,婉拒了孩子奶奶,根据我国法律,私下转送阿片类药物会有法律风险。
在小叶子离世的9天前,吴玲辗转找到了关注儿童安宁疗护的公益机构,在包括福川在内的社工帮助之下从一家医院开出了镇痛药,缓解了孩子的部分痛苦。但很快她就发现,口服药已经失去作用,因为孩子已经无法进食,她吃什么都会吐。
吃不进药的现象并不少见,到了后期,有些孩子会丧失吞咽功能,有些孩子吃了就吐。
林秋的小孩由于肿瘤已经长到脖子,进入熟睡状态后,颈部主要负责呼吸的肌肉群会相对松弛,反而导致肿瘤进一步阻塞他的呼吸道,让他喘不过气。郭艳汝记得,林秋最后求助于她的时候,孩子在家里已经处于快要憋死的状态。
如果能够获得医疗支持,孩子们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获得平静。郭艳汝说,如果能够在病房接诊林秋的孩子,她可以通过临终镇痛镇静的方式,降低孩子的意识水平,进而降低或者控制他感受到的痛苦,比如临终呼吸困难、濒死恐惧感等痛苦症状,都能得到有效处理。
这些孩子需要镇痛药,但需要的不止镇痛药。扎针上泵、基本营养支持、大便小便护理、口腔和皮肤护理、压疮护理……诸如此类,都需要医护人员介入。除此之外,家长还需要哀伤辅导。
安宁疗护除了对即将要走的孩子的疗护,其实更重要的,是要疗护孩子背后家庭的丧亲哀伤。
由于目睹小叶子在痛苦中离世,吴玲说,孩子走后,她每个月都需要花几千元钱去接受心理咨询。她也曾想过要去自杀,“就这么死掉去陪她”。后来,是想到了她的父亲,想到自己刚刚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不想让她的父亲再经历这样的事情,因此才打消了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