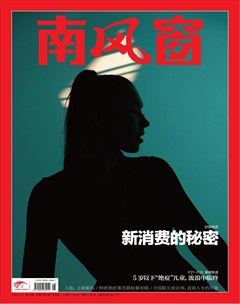“明天上午十点钟会有暴雨。”周霏强从口袋里把手机掏出,喃喃自语道。
3月初的杭州,全中国最炽热的目光都聚集于此。AI、机器人,来自赛博世界的风云和“六小龙”,搅动西湖一池春水。
但周霏强关心的是具体的天气。他是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副总经理。“雨来,骑车的人就会明显变少了。”
可是,AI都改变世界了,一辆自行车还重要吗?商业共享单车都进入成熟期了,一辆由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公益属性的公共自行车,还重要吗?
厦门、无锡、武汉等许多城市,都已经放弃了公共自行车。杭州为什么还要做?
当杭州站在AI时代的风口,用六小龙造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时,仍有人真切地关心每一场真实的风雨。
这是一项实实在在与人相关的公共事业,与机器人、大模型都不同。它不需要借助电波存在,关心的是最朴素的人民出行、休闲需求。它为赶路的人提供免费的“最后一公里”,也为畅游西湖的游客,献上本地化的无声陪伴。
2008年,杭州最早从欧洲城市“引进”落地了这项公共事业,为公众解决短距离出行需求。
当我们在追问,为何是杭州酝酿出科技六小龙时,回过头或许会发现,在骄傲的大时代里,杭州早已用一辆小红车,笼络住了普通人的一颗心。
骑
吴安家住湘湖边,小区门口列有一整排小红车。空闲时,他就会借一辆小红车,环着湘湖骑行。“从家里出发,跑一圈,正好回来还是还到那个点位,很方便。”
从2008年第一辆小红车投入使用到今天,17年的时间过去,似乎人们已经习惯街边停靠着一辆可以阶段性免费使用的红色单车。
西湖边的杨公堤,一辆从余杭区穿越而来的小红车,展示了杭州人民的“骑行力”——地图显示,从余杭区骑行到杨公堤,需要大约两个小时。
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总经理助理金根胜告诉南风窗,大部分市民的骑行需求集中在20分钟到30分钟之内,所以小红车首先可以免费使用1个小时。但通过“延时还”等叠加功能,最多是3小时免费,“三个小时有什么事情也都办好了”。
杭州人的骑行力,同样与城市规划的骑行友好理念密切相关。
绿野仙踪一般的杨公堤,非机动车道占了40%的道路宽度;在景区外道路的十字路口,非机动车道也拥有自己的右转辅道和红绿灯。柏油路平整,交叉口规则清晰,绿化带里种满各式各样的鲜花。2022年,杭州是唯一一个进入全球自行车指数前十的中国城市,排名第七。
背靠着完善的市政规划,在大部分城市无力支撑公共自行车运营的今天,“小红车”日租用量最高达到47.3万人次,免费使用率达到98%。
2012年,小红车用9处小红车点位的616吨碳排放量,从北京环境交易所换回了两万余元。这是一次公共自行车行业内绝无仅有的碳交易尝试。
一辆坚持绿色事业的小红车,也在坚持“与时俱进”。
不需要市民卡,不需要押金,部分车也不需要实体还车桩,还有临时停车和隔夜还车的选项。为了骑行的舒适度,其车胎换成了更减震的气胎,把速比调到了2.0比1,把脚踏板拉宽;为了安全性,亲子版小红车的后座,选择采用无缝钢管。
这些公共服务的概念,有时候仅仅只是为了改变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舒适度体验。
背靠着完善的市政规划,在大部分城市无力支撑公共自行车运营的今天,“小红车”日租用量最高达到47.3万人次,免费使用率达到98%。
各种细节,都似乎在提示小红车超长生命周期的唯一中心:读懂人。但一辆自行车如何能够看到全杭州人的需求?真相往往很简单:它的背后,有更多愿意为公共自行车事业付出的人。
红
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的人,穿着红色的厚外套,这是冬天或初春去点位值班的工作服。
夏天,这件厚外套就会变成红T恤或者红马甲,金根胜告诉我:“红色能让市民认出我们来。”因为小红车,也是红色。
小红车服务员张亚娟的红外套,一穿就是17年。作为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对外招聘进来的第一批员工,17年里她一直坚持着一套时间表。
早上7点,张亚娟会带着统一配备的工具包,准时出现在所管片区的小红车点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