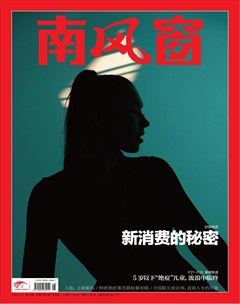大约从2024年9月开始,一条标语以不同形式频繁在北京的各条胡同里出现,它们有的是潦草的手写,有的是贴纸,有的是涂鸦,内容取自著名的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戈多明天准来。”
这不是人们约定好的快闪,也并没有明确的起因和影响,一句被不同的年轻人悄悄留在胡同里的标语,像某种无害的病毒一样复制、粘贴、传播,跟它的出处一样难以理解,但易于感知。
3月中旬,北京。我在距离东四十条仅两公里的工体,见到了两个“鼓楼青年”。他们跟我谈论自己的电影,提到《等待戈多》时,我想起了这个标语。
大豆和阿毛,两个在北京生活超过十年的外地青年,在2021年,因为太无聊了,拍了一部跟他们的生活一样“无聊”的电影。
电影叫《东四十条》,这也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电影的两个主角,一个叫东四,一个叫十条,他们在排一个不知所以的队的时候,碰巧穿了一样的裤子,莫名其妙成了朋友。有天他们在胡同捡到一张寻找走失赛鸽的广告,悬赏有十万元,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在北京找赛鸽。
2023年,《东四十条》在平遥国际电影节首映。红毯上,紧随那些国际知名的电影人、华丽耀眼的明星,出现了四个摇摇晃晃、手脚僵硬的年轻人,他们是《东四十条》的四位主创,导演詹涵淇(大豆)和覃牧秋(阿毛),东四和十条的扮演者杨凯航和钱赓。
今年4月,《东四十条》在全国院线上映。大豆分析了标记“想看”的用户画像,“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喜欢看文艺片、经常去独立书店的大学生和年轻人”。
有人笼统地称这个画像群体,为文艺青年。然而对大豆和阿毛而言,毋宁说这是一部关于“边缘”青年的电影。
《东四十条》是从边缘发出的呓语。但你仔细听,里面好像又有一些能被所有人理解的声音。
活动家与宅男
在大豆的讲述里,“共创”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有段时间,她跟几个玩乐队的朋友合租,感觉他们那种一起弹琴聊天共同创作的模式特别吸引人,后来她想,她无形中受到了影响,以玩乐队思维拍了《东四十条》,再大白话一点,就是“一起玩”。
刚来北京的时候,她是一个影迷。2013年,土木工程出身的大豆辞去工作,从浙江搬到北京生活。最开始她住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附近,这片俗称“小西天”的区域,是北京的文艺圣地。在资料馆看到了一刀未剪的《大开眼戒》之后,她开始“不断地”在资料馆看电影,认识了很多热爱电影的朋友,包括后来拍出《平原上的夏洛克》的独立电影导演徐磊。
徐磊制作电影的方法让大豆第一次意识到,拍电影还有一些“非主流”的方法,“你可以找平时总在一起玩的朋友,自己花钱去拍个电影”。
恰好这对大豆来说不算难。
她喜欢热闹的生活,再准确一点说,她喜欢感受人与人的连接,喜欢观察生活。
2019年,大豆跟朋友一起在鼓楼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月租金很高,所以他们把空出来的房间拿来做民宿,以此覆盖房租成本。某年中秋节,大豆叫了8个朋友来家里,计划每个人吃6只大闸蟹,准备了48只,结果朋友带朋友,那天晚上来到她的大房子的一共有48个人,她后来的搭档阿毛就在其中。
文艺青年扎堆的泛鼓楼地区,被称为“北京的布鲁克林”,是大豆和阿毛居住了十余年的家,也是电影里东四和十条常常混迹的地方。
阿毛跟大豆不一样,他“不上班”。他比大豆宅一点,喜欢在家里打游戏,当他需要解释一下生活,他总是拿游戏当比喻。2007年,他从广西来到北京上大学,此后再没离开过北京。从动画专业毕业后,阿毛并没有选择去动画公司工作,据说这个行业里,加班现象特别严重。后来他短暂地在一家APP研发公司工作过,但因为总是迟到被开除了。
上班似乎成了一件危险系数极高而回报率极低的事,于是他成为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上班有危险,所以阿毛选择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一直住在雍和宫附近。
两个人聊起拍电影这事,是2021年的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人就容易无所事事。他们没有什么组成搭档的意识,只是因为对方恰好跟自己一样没事做,又迫切想有事做。
大豆想得很简单:“有剧本,有导演,有摄影师,灯光可以没有,但要有录音师,还有一个人管饭——凑齐这些人,我们就可以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