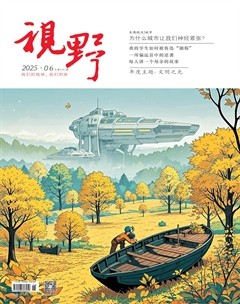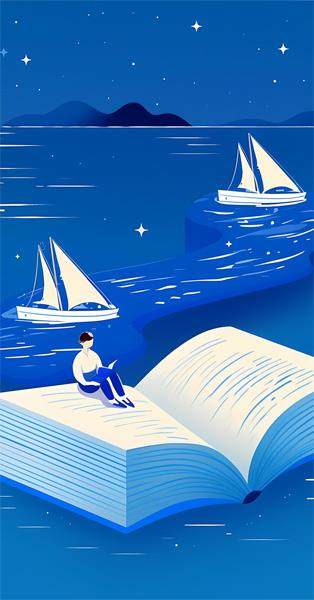
在我教他们的第二年,大概是讲完《藤野先生》之后的某个课间,有个学生和我说:“老师,我买了《鲁迅全集》!”这时旁边也凑过来一学生,带着点攀比的语气说:“我也买了,我早就买了。《呐喊》啥的,好几本。”接着,两个人亲切地讨论起来,带着点“他们都不懂”的神气。
追过星的朋友都知道,为偶像的作品买单,是“圈粉”成功的标志。为了让学生走到这一步,我做了许多尝试。所以如果老师在一开始就带学生看到鲁迅有趣的、生动的、能够牵引他们生活经验的一面,那么学生对鲁迅的初印象可能是“挺有意思”“挺搞笑”“嘴挺毒”。他们会在一层一层深入文本的过程中感受到鲁迅的炙热与深沉,自然就会对他生出又爱又敬的情感来。
严肃小老头?饼干圣斗士?
初中课本里第一篇鲁迅文章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讲课文之前我问学生:“你们心目中的鲁迅是什么样的?你可以用温度或者颜色来形容一下他吗?”
学生在小学时学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记得鲁迅给受伤的黄包车车夫包扎的故事;还能背出那首赞扬鲁迅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听了我的问题,纷纷举手发言:“30度!”“不!应该是水烧开的温度!”“如果用颜色表现呢?”“红色!”“黑色!”……
我注意到,很多学生没有说话,因为仅凭他们小脑袋里现有的信息,好像很难拼凑出一个人物的形象。于是我说,那咱们来采访一下“鲁迅亲友团”,看看他身边的人是如何回忆和评价他的:
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目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之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出仁爱和刚强。
——许寿裳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因为鲁迅先生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在关于鲁迅的回忆中我们发现,不同人眼中的鲁迅是不大一样的,学生尤其对萧红笔下贪吃的鲁迅感兴趣。我便给学生讲,鲁迅日记中经常出现“齿痛”,隔三岔五去看病,但又爱吃甜食,经常拐去稻香村买小饼干。
有一次朋友送他一包柿霜糖,鲁迅一尝就爱上了:“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许广平告诉他这是河南名产,用柿霜作成,性凉,如果嘴上生些小疮之类,一搽便好。鲁迅便感叹造化之妙,又无辜地声明:“可惜她说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收起,预备嘴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更好笑的是,鲁迅虽然自觉地把没吃完的收了起来,但却一直惦记着,后来实在忍不住,夜里爬起来又吃掉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孩子们天生喜欢听故事,尤其是这么“反差萌”的故事。“咳!原来鲁迅比我还馋呐!”在一片笑声中,大家一起打开了这位“饼干圣斗士”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居然是小朋友的自己人?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会让学生拍着桌子感慨“原来鲁迅小时候也这么淘”和“原来鲁迅也在课上搞小动作”的文章。
关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旨,教学参考书上给了三种说法:
(1)“批判说”,认为文章的主题是“揭露和批判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制度,表现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教育制度的彻底否定”。
(2)“儿童心理说”,认为文章表现儿童热爱自然、天真幼稚的欢乐心理。
(3)“对比说”,用百草园的自由快乐与三味书屋的枯燥无味进行对比,表现热爱自然的心理,表达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的不满。
说实话,大多数学生能在文中感受到的,恐怕主要是鲁迅对童年的怀念和不舍而已。那么更深层的含义要不要塞给学生呢?我选择直接把答案呈现在PPT上,让学生举手示意自己认同哪一点,结合文章说明理由。
很少有学生认同“批判说”,赞同此说的同学解释道:“先生拒绝回答‘怪哉’是何物,教我们读的书过于深奥,也不解释什么意思,可见这种教育是不好的,应该批判。”很快就有学生说:“但是‘我’在三味书屋也过得挺高兴的呀,可以出去玩,还可以上课搞小动作,三味书屋的生活也充满趣味,没有感觉到作者在批判呐!”
我追问道:“那么这些趣味是来自教学本身的吗?”
学生愣了一下,纷纷说那倒也不是。关于三味书屋的趣味,更多的是作者从枯燥生活里自己咂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