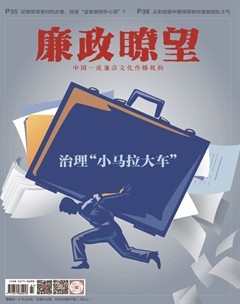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的一天,永康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旁人欢马叫。原来,唐高宗的宠臣李义府上书皇帝要求改建祖坟,把祖坟迁到风水更好的永康陵,唐高宗认为李义府孝顺便批准了这项工程。永康陵本是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墓地,李义府此举,无疑是想炫耀自己在皇帝面前有多得宠。
迁葬任务摊派到永康陵附近的八个县。三原县令李孝节最为积极,率先征调大量民夫和车马参与工程,其他六县令闻风而动,纷纷征集大批丁夫,昼夜不停劳作,争先恐后向李义府赠送迁葬所需物品。唯独高陵县令张敬业有点犯难,他不想劳民伤财征召丁夫,但又必须做出表态,于是亲自上阵下工地,最后竟因过度劳累而猝死于工地上。

据《新唐书》记载,迁葬工程极为盛大,赶来送葬的车马以及祭奠供帐等物浩浩荡荡,从灞桥到三原七十多里之间,相继不绝, “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比者”。而对于一名小县令之死,历史并没有费太多笔墨。张敬业之死,是古代基层官员生存的缩影,他们的苦楚与压力贯穿各朝。历代中央政府试图通过调整俸禄、强化监察来解决基层治理效能递减的问题,却因忽视“权力-责任-资源”的平衡而陷入恶性循环。
七品官乌纱背后的千斤重担
作为古代官僚体系的基层政治组织,县级政府职责繁重,县令或知县带着一帮胥吏拉着政务、军务、经济、教育、司法的“大车” ,面临豪强欺压、财政负担、自然灾害、上级逼迫等压力,常常身心俱疲、状况倍出。
居延(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酒泉市金塔附近)烽燧遗址出土的《居延汉简》记录了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档案和文献资料,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东汉永平五年(62年)秋,居延县令陈宣在油灯下加班批阅文件,突然被衙役急报打断,说城外戍卒因争水械斗,三人重伤,请他赶紧去处理。陈宣匆忙赶往现场调解,途中又遇农妇拦轿哭诉丈夫拒付赡养费。等到他处理完所有事情,几近天明,回到县衙,见案头已堆满治水方案、刑狱卷宗等文件。
据汉律的汇抄《二年律令·户律》载,“催婚”和“征兵”工作县令也得负责。“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县令需定期核查婚配情况,甚至动用戍卒充当“相亲信使”来为“晚婚”女士做媒。此外,征兵任务繁重,如东汉末年为应对战乱,县令需完成“三人抽一丁”指标,面对逃役者时需采取强制手段,常激化官民矛盾。
唐代监察御史韩琬对基层之难深有体会,他曾挥毫写下辛辣的官场生存指南《御史台记》,书中那句“入县令为畜生道”的戏谑之语,如利刃般剖开了这些基层官员的生存困局。
明朝为了防御蒙古的侵扰,朝廷沿长城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大同(今山西大同县)为九镇之一。此地设有专属监察机构巡抚大同都御史,其职权跨越军务与民政,可直接弹劾总兵至县令等各级官员。这样,大同县令被摆在了很尴尬的位置,他头上那顶七品县令的乌纱帽,几近成了权力绞盘下的催命符。
朱元璋第十三子代王朱桂在大同纵马游猎、强占民女,经常欺压百姓,甚至袖藏铜锤在街头伤人。百姓擂鼓鸣冤时,县令却只能紧闭县衙,因为按《大明会典》,皇族案件须交宗人府,县令连案卷都无权过目。在大同城池的另一边,正二品总兵府十五万边军截留六成耕地为军屯,县令的司法权在边军的铁蹄声中已被碾作齑粉。
嘉靖朝时,总兵仇鸾部卒当街劫掠,大同县令张文奎刚欲查办便遭“通敌论斩”的死亡威胁。到了崇祯时期,县令张宗衡在《边镇十弊疏》中悲叹“县令非官,乃军门之胥吏;县衙非署,乃总兵之库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