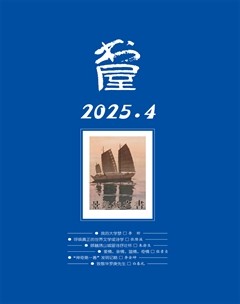一
1935年,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1936年,鲁迅去世后,钱玄同撰文纪念,提出他的三个“短处”:多疑、轻信、迁怒。
一个人童(少)年时期的创伤,会影响他一辈子。能够超越的,寥若晨星。很多人是蒙昧无知,倒相安无事。如果觉悟了,反观自身,就很危险。鲁迅在《野草·墓碣文》中写道:“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又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大概是自画像。“抉心自食”,可以说是鲁迅一生的写照。
鲁迅自己也多次说到自己的“黑暗”。他说:“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是究竟是否真确,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能邀请别人。”他又说:“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周作人说他是“虚无主义”,不是没有道理。
众所周知,一个人性情养成的最关键时期是三到十五岁左右,也就是童年、少年时代。太早没有记忆,太迟影响也就有限。鲁迅正是在十三岁遭遇家庭变故,忽然从小康之家坠落下来。多年后,他在《呐喊·自序》里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这种“侮蔑”是周作人没有体会到的。1922年12月,鲁迅已经四十二岁了,他写作《呐喊·自序》时,还在痛苦地嘶喊:“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每次读《呐喊·自序》,我就无法自制,会被深深地带进去。其实,鲁迅的文字都有这种情感,让人无法拒绝和逃离。他在厦门时,《写在〈坟〉的后面》一文写到夜的体验,真是令人无法释怀。还有《怎么写——夜记之一》说,“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提到窗外的丛冢、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和前面的“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都是读者很难忘怀的文字。
鲁迅的创伤性记忆,一是他少年时家庭的变故,祖父入狱,父亲病逝,家道沦落,备受族人的欺辱和旁人的歧视。他在自传中说,“到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写作《呐喊·自序》的时候,鲁迅已是中年,名满天下,回忆当年,还是创痛至巨,《父亲的病》也是血泪斑斑。
二是母亲给他娶的妻子朱安。我曾撰文认为,没有朱安,周树人就无法脱胎换骨成为“鲁迅”。因为朱安,鲁迅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一直过着独身生活,长期的性压抑对他的性格、心理肯定会有大的影响。他之所以仇猫,不能说没有这个阴影。《寡妇主义》一文中,他写道:“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酸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
1910年11月15日,给许寿裳的书信中,他说:“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