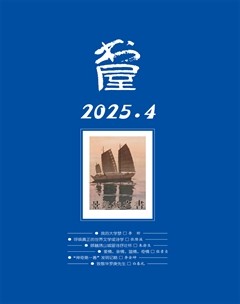一
佛教是古老的宗教。寺庙历来是文人墨客参访问道的重要场所。苏轼对于寺庙、对于僧侣是敬重的,早年在四川时,就游览了成都的大慈寺和胜相院,认识了惟度法师和惟简法师,听他们讲佛和历史掌故,受益匪浅。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三苏父子启程赴京,一路走走停停,寺庙成了他们歇脚投宿的好去处。苏轼也有“过宿县中寺舍,题老僧奉闲之壁”(《和子由渑池怀旧·自注》)的记载。至京师后,父子三人暂无安顿之场所,遂寄居于兴国寺浴室长老德香的院中,在此备考。三十多年后,苏轼闲暇之余,多前往兴国寺浴室院游观,发现中书舍人彭汝砺“亦馆于是”。岁月沧桑,物是人非,“院中人无复识予者。独主僧惠汶,盖当时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导予观令宗画,则三祖依然尚在荫翳间”(《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并叙》)。之后,苏轼又携秦观来此拜访僧惠汶。秦观得以“始识汶师”,“后二年复来,阅诸公诗,因次韵”。后陈慥“寓棋簟于”太平兴国寺,苏轼与范百禄更是“数来从之”。
嘉祐元年秋,苏氏兄弟二人在开封景德寺应试。苏轼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开始崭露头角,名满京城。当时,苏轼才情舒张,继续住在兴国寺备考礼部会试,越明年,以《刑赏忠厚之至论》惊艳四座。然不久,其母程夫人病逝,苏轼兄弟及父亲苏洵只能返回故里。至嘉祐四年(1059)四月,守孝期满,父子三人决定举家离蜀,再往京城。
苏轼凤翔期满还朝,获得个虚职殿中丞,至治平二年(1065),原本想谋一番作为的他失去了妻子。丧妻之痛对苏轼打击甚深,后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为证。再过十一个月,父亲苏洵病逝,这对于苏轼来说,可谓悲切痛心。治平三年(1066)六月,苏轼、苏辙兄弟扶灵返回故里,一舟两棺,着实凄凉。人生突变,尤其在生死面前,人变得如此渺小。也或许是岁月磨难,生死冲淡光芒,消磨了韧劲。待守孝期满,苏轼再度还京,已是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了。苏轼因应试声名鹊起,从嘉祐元年至熙宁元年,已历十二年多的时光,其间,虽然谋得一些职位,但多为闲散之职,在朝廷也与主政者政见不一,多少有些郁闷,相比当初的高光时刻,产生了心理落差。更为不幸的是,在这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失去了父母、妻子,两度守孝。在不幸和磨难之间,在生死茫茫之间,苏轼访寺寻僧的心态、心境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熙宁四年(1071),苏轼任杭州通判。到任三日,苏轼就前往西湖孤山访问惠勤、惠思二僧。孤山幽深,古刹名蓝,苏轼到访后,心情舒坦,作《腊月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访僧问道,不就是寻求内心的平衡、平静吗?此时经过仕途颠簸周折、尝尽人生苦辣酸甜的苏轼或许正需要这样的平衡、平静,也因此,他和僧人达成了一致,彼此心近了,多了理解和认同。
杭州名刹众多,高僧亦多。原本对佛寺甚喜的苏轼,此时便与僧侣有了更多的交往,有的甚至成了他一生的挚友。“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时以诗赠名僧清顺、可久二人。可久工于古诗、律诗,居祥符寺,清苦耿介,不善与人交往。“门前歌鼓斗分明,一室清风冷欲冰。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青灯无语,岁月静好,尘俗罗网,不过是自寻苦恼罢了。仕杭州,在苏轼人生履历中,不算发配,也谈不上苦难悲壮。但大抵是从这个时候起,苏轼大量涉猎佛事,访僧问道,参悟世事,研究佛典,这或许是他排解内心孤独的需要,也或许是人生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对万物有了自己的认识。
在杭州期间,苏轼与高僧往来频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位。一是上天竺的辩才法师。辩才名元净,乃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弟子,道行高深。“即之浮云无穷,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吐雾之中。”(《辩才大师真赞》)当时苏轼次子苏迨体弱多病,三岁仍不能走路,苏轼送苏迨至辩才法师处落发,取名“竺僧”,后苏迨行走自如,苏轼感念:“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赠上天竺辩才师》)苏轼对辩才法师多有尊重,称其为“老师”,“取老师意,剃度一人”(《与辩才禅师二》)、“闻老师益健,更乞倍加爱重”(《与辩才禅师四》)、“老师必能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与辩才禅师五》)等。后苏轼从杭州还朝,对辩才甚为思仰,“别来思仰日深”(《与辩才禅师五》)。
苏轼在天竺寺与另一高僧慧辩禅师也交往频繁。慧辩大师与辩才大师同是明智大师弟子,善思辨。苏轼常前往与之参悟,听其宣讲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