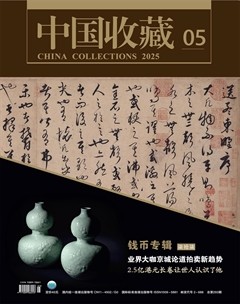北方辽宋钱币窖藏中常常出土一些唐宋面文的非官炉钱。这些钱币风格多样,明显不是同一处铸造,笔者更倾向将其统称为“西北类”。这些西北类钱币存世量大,很多时候有固定的版别,甚至很多版别之间还有相同的风格,说明其铸造时有一定规模,有别于普通民间的私铸。由于这些钱币种类繁多,无法一一详述,因此笔者只着重讲述与这种治平通宝背星版风格相似的一类钱币。
并非官方所造
以治平通宝背星版为代表的这一类钱币(后文将这类钱币称为“星纹手”)有如下特点:首先是铸造较为精美、足值,大多数虽然直接以北宋普通流通钱做模,但经过翻砂后,仅仅砂性略大,文字仍然清楚,与普通北宋官炉钱无异,直径和重量上也没有明显减少。其次是含铁量较大,很多在出土的同时就伴有铁锈,绝大多数都有或强或弱的磁性,用磁铁能直接吸起。最后是背面内郭都或多或少呈现反郭特征,几乎没有平背现象,个别品种(不只局限于治平这一种面文)背面有星纹,这是铸造时有意后加的固定版别,非流铜。
由于仿铸质量较好,《北宋铜钱》上将这种治平通宝背星版以及与之相同的很多星纹手都收入其中,且并未作出格外标注,可见编者将这些也当作了北宋官炉钱。其实通过后两个特征,可以将其与北宋官炉钱区别出来。过去有泉友将这类钱币称为“助国手”或“辽铸”,两种说法如果仔细来看都不准确。先说助国手,日本钱谱又称“牡(壮)国手”。顾名思义,就是风格类似壮国元宝、助国元宝的一类钱币。参考前文所述的星纹手的特点,可以明显看出助国手与之的区别。首先,助国手多数都是模仿助国、壮国钱的新规书体。其次,助国手铜质较好,大多不含铁。最后,助国手背郭较为精整,几乎没有反郭纹。此外,星纹手钱币分布较为广泛,几乎包括了整个宋辽交界区,并且很多还流通到了辽、夏内地。而助国手大多数出土于赤峰附近,空间分布不同。
再看辽铸这个说法。这类钱币虽然与辽朝有很大关系,但也不可能是辽朝官方所造。通过如今所见实物来看,辽朝铜钱含铜量较高,基本在80%左右,因此出土时大多都泛红色,而星纹手出土时都是和普通宋钱一样的青色。且辽朝官炉钱大多铸造粗糙、穿郭不整、文字隐起,星纹手却体现出了相对较高的铸造水平。通过实物合金成分和铸造工艺来分析,两者无多大关系。

从当时的经济环境分析,辽朝高层大抵也没想到或没做到大量仿铸宋钱来填充市场。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而以皇帝居于北方,中枢决策机构属于北面官。我们不妨来看当时的北面地区,也就是契丹腹地是什么样的经济状况。首先要肯定的是,经历了封建国家的建立,辽朝商品经济总体得到了一定发展。“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上下相师,服御浸盛,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表明契丹建国后社会增加了对钱币的需求。但这种需求并不是很多,因为物物交换基本可以满足经济的发展。胡峤曾在《陷北记》记录辽上京的情况:“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可见契丹建国后,即使到了太宗、世宗、穆宗时期,以布帛为主的实物在商品交换中还占有极大比例。并且在之后的商业发展中,布帛一定程度出现了可以替代铜钱的一般等价物的特征。统和三年癸巳,辽圣宗曾下令“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道宗咸雍七年(1071年)四月又下诏“禁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等。学者何天明指出,“行在”一词指皇帝出巡的住所,也就是说这些管理禁令发生在契丹腹地。这两点很值得注意,因为若是简单的物物交换,那么完全可以按照布帛自身的尺寸,去交换和其等价的货物,无需在意到底中不中尺。当需要用一定的尺作为衡量单位去衡量布帛时,表明布帛在交换中已经出现了相对规范的货币单位,也就是史料中所提到的“尺”。在商品交换中,人们看重的是布帛的单位(面额),而非布帛本身尺寸、大小、质量等所能实现的实用价值。有布帛作为交换的媒介,铜钱的需求量就更小了。
再来看辽朝官方对这一时期货币铸造的态度。无论是太宗时“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还是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实为刘仁恭)所藏钱,新旧互用。“由是国家之钱,演迤域中。所以统和出内藏钱,赐南京诸军司”,都展示出了辽朝统治者积极接受货币的事实。但统治者似乎也只局限于积极接受,而非积极铸造。赵志忠《虏廷杂记》记载:“景宗朝,置铸钱院,年额五百贯,则契丹铸钱旧矣。”这里铸造的钱未点明是什么面文,但这并不重要。如果仅仅是年铸额五百贯,对于庞大的国家完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即使到重煕以后辽朝开始大量造钱,所造的官方年号钱也较为少见,存世量远少于这些星纹手钱币。

所以,虽然随着社会发展,辽朝统治者一定程度提升了对钱币流通的重视,但这个程度并没有多高,且并没有增加对铸造钱币的重视。应当可以肯定,这类星纹手钱币并非出于辽朝北面的官方所造。结合这类钱币多于辽朝南方及宋辽边境出土,笔者认为这些钱币或许与辽朝南面官管辖下的汉城有关。以星纹手为代表的多数西北类钱币的来源,很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汉城自身私铸或半官方铸造,用于满足自身的流通;第二个是随着榷场贸易,北宋沿边地区所造的输辽私铸钱。
制度差异所致
南面是汉族聚居区。契丹统治者实行因俗而治的南北面官制,就表明了南面汉城地区与北面契丹腹地有极大不同。南面汉城铸造和使用货币的历史由来已久。与辽年代较近的桀燕在这一地区流通铁钱、泥钱,造成了经济混乱,这本身就可以说明此地当时已经普遍接受了以钱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经济。为此,在南北面官制中“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也是对南面地区经济相对繁荣的肯定。南面地区是否缺少铜钱?答案是肯定的。北宋实行铜禁政策,禁止铜钱输出,“四月十五日,刑部奏:‘定州乞申严,自今将铜钱出雄、霸州、安肃、广信军等处,随所犯刑名上各加一等断罪。’从之”。虽然北宋每年向辽缴纳数额不菲的岁币,但这些岁币是由绢和银组成,没有铜钱参与。并且所交岁币直接由辽朝中央机构收纳,并不能直接惠及南方地区。
此外,宋人曾经说“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所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也就是说北宋缴纳的税币,很大一部分都通过贸易顺差又被北宋挣了回去。而宋辽主要贸易地区都集中在辽朝南部,北宋挣取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辽朝南部有极大的货币流失风险。南面地区铜钱流入少、流出多,北方中央又不肯铸造更多铜钱以供使用,为防止钱荒发生,必然产生两个主要应对手段:一是自己暗中铸钱以满足流通,二是积极从宋朝走私铜钱。现在来看,这两个手段都是可行的。针对第一个手段,辽朝上层的政策是禁止私铸,但效果不佳。
本身在南北面官制设计过程中,南面官以及相关的货币管理机构就具有冗杂混乱的特征。依靠南面官去禁止私铸,必然不太可行。学者张澍才曾提到辽朝多次禁止私铸,反复禁止私铸,某种程度可以说明禁令的执行效果不好,也就说私铸仍然兴盛。第二个手段同样取得了较大成功。《宋史·食货志》中明确记载了北宋景德初年“复通好……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粳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等,可见铜钱在榷场贸易中已经被直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反映出的是辽朝方面对铜钱需求。熙宁年间开放铜禁时,更是出现了“边关重车而出,海船饱载而归的盛况”。如今辽代窖藏中北宋钱币占绝大部分,本身就能说明第二个手段执行的成功。苏辙在《栾城集》中说:“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有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宋人对辽地大量行使北宋货币呈现出惊讶和担忧的态度,同样也能说明北宋铜钱流入辽地数量之多,让宋人始料未及。我们有理由相信,宋朝边民在走私铜钱时,除了走私正常的北宋铸币,很大可能也会自己铸造并走私轻薄的私铸钱币以获取暴利。“雄州、广信、安肃榷场,北客市易,多私以铜钱出境”。这里的“私”,可以理解成走私铜钱,当然也有可能指的是私铸铜钱。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发展,辽朝南面地区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大。伴随着辽宋双方本身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因素,催生出了以星纹手为代表的西北类钱币,其最终的目的都与满足辽朝南面汉城地区货币流通有关。
针对单独的星纹手这一类钱币,综合上述结论,笔者认为其应当是辽朝南面一些汉城地区铸造。从形制上看,这类钱币重量足值,工艺与风格稳定,铸造技术较高,并且一部分有后添加的固定的星纹记号作为某种标注,体现出其铸造时有一定的规模与组织管理结构。这不太可能是北宋地区人们偷偷私铸的结果,而是辽朝南部官民对通货紧缩现状产生共鸣的结果。面对通货紧缩,为了确保私造的货币能够更容易使市场接受,达到满足市场稳定运行的目的,必然要铸造的和当时普遍流通的北宋钱质量基本一样。这种情况在明朝中期也有所体现,且这一点也是北宋地区以走私牟利为目的的民间私铸所无法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