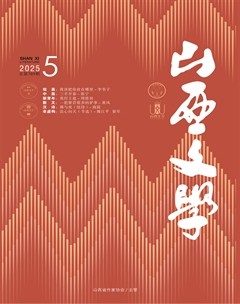顾拜妮:晨蕾你好,欢迎参加步履对话,你的小说《黑白照片》发表在“步履”栏目2023年第9期,还记得当时写这篇小说的一些细节和初衷吗,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个故事?你如何看待小说里的女性移民形象?
王晨蕾:谢谢拜妮的邀约。现在再回看,《黑白照片》好像算是我关于英国写作的一个句点,或者至少是分号。那之后我就很少写英国故事了,因为回忆能够提供的素材越来越少。其实当时写这个故事的动机特别随机。2019年夏天我在英国做实习,当时的老板住在斯旺西的一个沿海小镇,有几次我们去他家里拍摄素材,他家那种精心维护的温馨氛围对我这个穷学生产生了一点儿冲击,但比起所谓的阶级感,我看到更多的其实是文化差异。我觉得西方人确实比我们更注重生活,而这一点在居住环境方面体现得特别突出,他们会把家里弄得很舒适,花心思去营造细节上的愉悦,比如他们会买那种很不显眼的艺术品放在家里的角角落落,虽然装潢并不华丽,但特别具有整体的美感。你会觉得“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生活的空间、一个安享亲密时刻的地方,不仅仅是为了睡觉吃饭,更与“面子”无关。所以当我想写一个关于英国中产生活的故事时,我立刻就想到了那个老板的家,小说里的环境描写也大多借鉴于此。
但毕竟我的主角得是中国人,从自身经历出发,我决定写一个年轻的女性新移民形象,其中自然就包括了一些对移民群体的社会文化身份的思考。我最终选择用男性第一人称去写,是因为这更好地服务这篇小说的叙事,方便“我”对女主角投射一些外部目光。简单来说就是我需要跳出我自己的性别身份和处境,去对这个女人进行某种社会的集体性的凝视——这里无疑和性别议题相关了(但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复杂)。与此同时我又很难不共情她,所以写出了一个偏“弱”的男叙事者,摇摆、被动、多愁善感、内心充满矛盾,被女主人公吸引但又对她不无偏见,我觉得“我”所提供的这么一种缺乏传统意义的“男子气概”的视角是这篇小说的关键之处。这么说起来,感觉有点儿像是“为了碟醋包了一盘饺子”,不过说实话,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是这么来的。
顾拜妮:你毕业于英国卡迪夫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我们联系的时候,你正要辞掉北京的工作,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攻读电影研究生学位。为什么选择重新回到校园,从直接触碰社会现实到采用一种更加迂回和艺术的方式来关注生活?
王晨蕾:从新闻转向电影算是我做出的一个职业选择吧。我挺理想主义的,以前还有点儿个人英雄主义,小时候想通过学新闻、做记者“拯救世界”,后来从事这个行业,慢慢就忘记了早先的想法。我是个很容易放弃的人,情感极度脆弱,没什么韧劲儿,所以决心把自己“去政治化”,去追求艺术,在美学中尽情享乐。学了电影之后发现,艺术只会更“政治”(苦笑)。所以我现在也并没有变得更“平和”……不过我还是会在艺术这个更——如拜妮所说,“迂回”的——道路上继续下去,因为相比于新闻媒介,艺术总是给人留下一个更宽的口子,在这个开口处每个人都可以有更多自主地阐释和思考。与其去演讲,我更想做些有趣味的、能娱乐大家的东西——也就是艺术创造。“流血流泪”都是我自己的事儿,观众不需要知道。
顾拜妮:你的小说大多关注海外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其中不乏一些小小奇遇,《黑白照片》也是如此,一次普通的人像约拍,让主人公闯入一个陌生的跨文化家庭,隐隐发现这个家庭的一些秘密,却又没有完全展开,留给读者更多思索和想象的空间,你是怎样看待留学生这个群体的?以及你作为留学生有没有经历什么难忘的奇遇?
王晨蕾:海外留学生的故事对我来说最好写,因为我可以直接从生活中获取灵感,但它同时也是我现阶段最想写的,一方面因为我一直希望我的小说能够传达某种人的个体性和孤独感,另一方面我也想借创作表达一些自己对“跨文化”这个全球化现象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