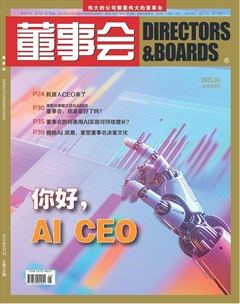在证券犯罪追责加强趋势下,厘清并正确把握行刑双向衔接在证明标准、程序处理、证据审查以及认定逻辑层面的核心差异,有助于推动行政处罚、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有效运行,有助于证券违法治理走向现代协同治理
2024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出台《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从严治理为核心理念,提出“应移尽移”等要求,系统构建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行政处罚、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我国证券违法作为典型“行政犯”的背景下,随着《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修订施行以及最高检与中国证监会联合政策导向的强化,证券犯罪追责呈现明显扩张趋势。
当前,重点打击领域涵盖信息披露违法(欺诈发行、违规披露、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及中介机构执业失范等典型犯罪类型。在案件进入实质程序前,相关主体需着重把握行刑双向衔接的四大核心差异:证明标准层面,行政程序的“优势证据”与刑事程序的“排除合理怀疑”存在证明强度梯度;程序处理层面,需协调行政调查时效性与刑事侦查周期性的制度冲突;证据审查层面,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需遵循法定程序要件;认定逻辑层面,行政违法性判断与刑事可罚性评价需构建递进式分析框架。这些差异构成行政处罚、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基础。
证明标准不同:不“刑”未必不“行”
在刑事追诉与行政处罚中,必须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及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正当程序;其间,对违法行为的举证过程是确认事实问题的关键环节,而证明标准的设定则直接关系到司法及行政部门最终对违法行为的认定。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院需要达成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且证据确实充分,结合刑事诉讼法(2018年)第五十五条规定,具体表现为: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而在行政处罚中,中国证监会证明则仅需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例如《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已失效)第二十六条规定“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应当适用明显优势证明标准”。那么,上述证明标准的差异如何在行刑双向衔接的程序上体现?
首先,对于“先行后刑”的情形,由于证明标准不同,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未必会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例如,新疆证监局〔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李某刚构成内幕交易,并对其处以25万元的罚款。但针对该案件,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检察院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认定,认为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最终决定不予起诉。可见,中国证监会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不能天然证明当事人存在刑事责任,案涉事实仍应经过刑事标准的检验;当然,司法机关不认可也不代表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决定错误,问题核心在于两种程序下适用的证明标准存在差异。
其次,对于“先刑后行”的情形,即使刑事司法机关未对当事人追责,中国证监会也可予以行政处罚。例如,在周继和内幕交易案中,当事人主张公安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并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其不应受到行政处罚。最高法在行政诉讼中做出(2017)最高法行申8678号再审裁定:四川省公安厅……做出川公直(经)终侦字〔2015〕01号《终止侦查决定书》,以“证据不足”决定终止对周继和的侦查程序,系刑事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不符合刑事追诉标准做出的独立判断,并不影响之后行政处罚程序的进行,不能成为中国证监会做出被诉决定的程序阻却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