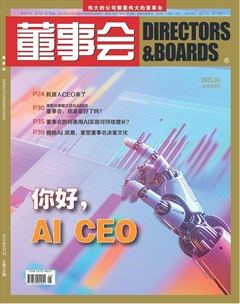上市公司设置首席治理官,既符合公司治理的国际发展趋势和良好实践,也有助于破解目前制约董秘有效发挥公司治理角色的制度障碍。推动这一公司治理实践有效落地,离不开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的引导、优秀企业的引领以及市场力量的推动
国际上已有较多大型企业设置首席治理官,反映了在公司治理监管要求(特别是信息披露透明度要求)日趋严格,公司治理工作专业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以及董事会独立性显著上升背景之下,提升公司治理合规性和运行有效性的需要。由于公司治理相关事务是董事会秘书(以下简称“董秘”)的核心职责,董秘具有法定高管地位且处于联结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位置,由此董秘担任首席治理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董秘转型为首席治理官,发挥公司治理合规性守护者、公司治理有效性促进者、董事会和董事高效履职赋能者、公司治理最佳实践推动者、利益相关者联结者角色,有助于完善董秘制度,推进中国公司治理现代化进程。推动中国董秘转型为首席治理官,需要监管机构、行业协会、机构投资者、评级机构和公司治理领先企业的共同努力。
公司治理的实践发展呼唤首席治理官
进入21世纪以来,公司治理领域的监管合规要求越来越严格,公司治理在董事会议程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客观上需要高级管理层中有人负责对接和落实董事会对于公司治理议题的关注,而首席治理官这一高级管理岗位也应运而生。设置首席治理官并由公司秘书/董秘担任,正在成为公司治理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
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司秘书行业自律组织“特许秘书与行政管理人员公会”于2019年9月正式更名为特许公司治理公会(CGI),并授予特许秘书和公司治理师两大职业资格。在CGI的九大属会中,英国与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中国香港等主要属会,均已更名为“公司治理公会”。世界银行所属国际金融公司(IFC)在2016年《公司秘书:治理专业人士》的调研报告中,提出用“公司治理官”或“公司治理总监”来取代“公司秘书”职务头衔。而在国际知名大企业中,首席治理官兼任公司秘书,已是较为常见的做法。例如,雪佛龙公司的玛丽·A.弗朗西斯自2015年起至今一直担任公司秘书和首席治理官;艾琳·泰勒则从2019年起一直担任汇丰控股集团的公司秘书和首席治理官。
由公司秘书/董秘担任首席治理官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和现实上的必要性。从公司治理的原理来看,“首席治理官”本是董事长的职责,因为董事长就是董事会的领导人和治理层的首脑。然而,董事长亲自担任首席治理官又是不现实的,既没有负责公司治理具体事务的足够时间和精力,通常也缺乏公司治理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将“首席治理官”职责授权给董秘行使就成为一项合理且可行的选项。公司治理相关的事务本来就是董秘的核心职责和本职工作董秘处于联结董事会和管理层、上市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有利位置,且具有处理公司治理事务的必要知识与专长。
董秘担任首席治理官,通常能够在三个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促进公司治理体系的合规有效运行。第一,显示公司治理层和管理层对于公司治理工作的重视,有利于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增强投资者对于公司以“善治”提升股东回报和投资价值的信心,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品牌、声誉和估值。第二,有利于推动董事会的实质有效运行。在董事会独立性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董秘作为首席治理官能够赋能董事会的有效运作和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的有效履职,促进董事会充分发挥战略决策功能,并督促管理层落实董事会的战略决策。第三,有利于发挥专业化分工优势,提升公司治理相关工作的效率。董秘作为公司治理高级专业人士,担任首席治理官可以实现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合规成本、减少监管处罚。
中国董秘转型首席治理官具有现实必要性
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上市公司董秘制度以来,人们对于“秘书”职业存有刻板印象,导致董秘虽然享有法定高管地位,但围绕董秘的“身份”和职责,社会上仍然存在普遍的误解。例如,董秘被许多人认为是董事长的生活秘书或行政秘书,将其视为无足轻重的角色。为了体现董秘的高管身份,有观点认为董秘可改称为“董事会秘书长”。然而,“秘书长”这一称谓明显带有行政色彩,与董秘职业生涯的市场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趋势并不相符。
自1993年公布并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正式引入董秘制度以来,董秘已成为公司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而董秘制度也已成为中国特色公司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董秘制度在实践中不断趋于完善,但现实中仍然存在诸多制约董秘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环境与制度因素。具体而言:
第一,公司法一方面赋予董秘上市公司高管地位,但另一方面又按照“公司秘书”确定董秘的职责范围,基本上是会务筹备、文件保管、信息披露等事务性工作,由此造成董秘的法定高管地位与法定职责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不匹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