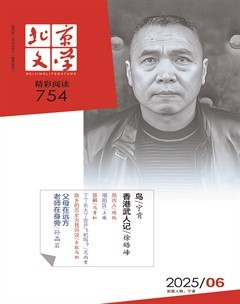消逝即永恒(评论)
我们每一个时刻都在经历消逝,这是危机,也是契机。然而人们还是常常因此感到忧惧,而唯其追忆和纪念、讲述与重塑,或有复活的机缘,毕竟只有遗忘或无视才是真正的消亡。因而所有的一切,都将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留存自身并重新赋形。
宁肯中篇小说《鸟》是其“城与年”系列小说之一,通过邬晓永与“我”的交叉回忆,叙写二十世纪后半叶北京市井生活,以孩童视角来写永和小芹的交往与成长史,反思家庭生活的纷繁与宏大历史的复杂,直面个体成长的创伤性时刻及其诊疗。邬晓永生于1959年,小时候常被束缚在床上而成其伤痛体验,与小芹被管制和欺侮等形成了呼应。在这其中,“鸟”的意象成为了显在的隐喻,那是被缚的现实与渴求被解救而不得的无力感,“我不会对鸟不解,但对哥哥姐姐不解,甚至也对所有‘人’不解。”他们后来把死去的鸟埋在了胡同的老榆树下,在残酷的生活中始终留存简单而坚韧的温情与爱。
当然其中也经历着诸多的不可能——小说中,成长的过程便是经历蜕变时无不包孕着痛苦和煎熬的经验累积,譬如永目睹了鸟的整个死亡过程哀伤不已,然而这样的亡逝不仅成为他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所在,也是他疗愈甚至拯救自我的药方;最终与小芹包括与北京的别离、对难以尽述的亲朋的怀念,以及不断“聊起”而形成追忆的数学家姐夫及费马大定理,等等,不是所有的鸟儿皆能在天空翱翔,“我”们也始终为人世间所羁绊和牵累,无可奈何,又念兹在兹。
可以说,宁肯的“城与年”系列实际上指示的是空间和时间的交汇——就在当下时间被泛化和悬置,而空间被无限放大的文化语境中。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北京文学》2025年6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