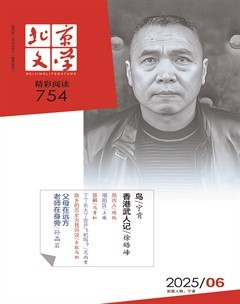布是人类文明的又一个源头。人能体面地活着得感谢一种植物,叫麻。人能高贵地活着得感谢一种动物,叫蚕。人对美好向往又得感谢一种工匠,叫绣娘。一方绣花手帕,一双 “喜”字鞋垫,一个肚兜或口围,一对绣花枕头,一顶百花帐,曾寄托多少青春男女的梦想。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田园生活无非是吃饭、穿衣两件大事。《说文解字》:“布,枲織也。”枲即是麻。《诗经·东门之池》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在约五六千年前,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步入鼎盛时期,人学会提取野麻纤维,用石轮或陶轮搓捻成麻线,再织成麻布。后又从“剥茧食蛹”中发现蚕茧可以抽丝,嫘祖养蚕缫丝,纺锦织绸。丝绸的稀少决定着人的等级。苎麻主产于南方。王祯《农书》有:“南人不解刈麻,北人不知治苎。”江西是优质苎麻的主产地,苎麻织夏布,古有“豫章织绩苎布工细甲天下”。2600年前,江西古越先民就开始在麻布上印花。夏布轻如蝉翼,薄如宣纸,柔软润滑,平如水镜,轻如罗绡,唐时列为贡品。以夏布做绣底的夏布绣有可能更早,到北宋已有雅俗之分,雅者为夏绣,俗者为麻绣。
夏布绣兼容夏布的自然肌理和水墨丹青的绘画神韵,其色泽古朴、典雅深沉,针法灵活多变,有粗犷、地域鲜明、拙中寓秀的独特艺术风格和语言体系。夏绣是继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之后的第五大绣种。
仙女湖有一个绣娘叫张小红,当今被誉为“中国夏布第一绣”。新余仙女湖是传说中“七仙女下凡”的地方,也是《天工开物》的原创地。张小红已逾花甲,看上去仍优雅端庄,有仙女的灵气,又有绣品的清纯脱俗,让人眼前一亮。
新余有亚洲最大的亚热带树种基因库,苎麻遍地生长。古越先民曾创造了一种镜像,“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种苎麻,做苎布,于我亦不陌生。小时候,鄱阳湖北岸谁家不种三五分苎麻?苎麻生命力极强,埋几棵麻蔸,来年便长成一片。苎麻一年收三季,收割苎麻很苦。第一季收割在五月,苎麻有一人高,人在麻中不见人。苎麻不是用刀割,而是靠手去劈,村里人叫“打麻”。先用小竹棍把苎麻叶子打掉,然后弯下腰,左手折断苎麻,右手食指于断开处快速滑动,将麻劈两半,白色麻秆飞出,手中留下两片麻皮。二分地的苎麻从大清早要干到晌午。苎麻皮挑回家,先浸泡在池塘里,吃完饭,再掏出来剥麻。剥麻就是去麻皮。去麻皮的专用工具是一个小弧形铁刀,套在大拇指上。食指与大拇指按住,下口要准,力道要稳,麻皮才能一次脱干净。如果麻皮一次脱不干净,麻色就不明亮,晒干的麻丝就不白。麻丝挂在竹篙上,遇上大太阳,晒一天就够。遇上阴雨天,麻丝不能快速干掉,麻色就隐晦难看。打麻和剥麻都是女人的活,女人腰身活泛,做事细致。当然,也有手脚灵活的男人既打麻,还能剥麻。剥麻会在手指上留下麻渍,深褐色,极难洗掉,羞于伸手见人。
还有一道工序叫绩麻。取出麻缕,将其浸泡在清水中,将浸麻缕一根根劈开成丝。取出两根劈开后的麻丝,将末端搓捻在一起。同方向从交点处再次搓捻,利用捻度使其自然咬合紧实。两根麻丝就“绩”成一根。绩麻是个细致活,一天也难绩二两麻。绩麻之后是卷纱。用纺轮把麻纱卷到纺锤上,再织布。织布更专业,需绑上腰带,整好经,脚踏纺车,手甩梭子,梭子带动经线。随着织布机 “嘎吱、嘎吱”的声音,又密又实的夏布源源不断地吐出来。在未见“洋布”之前,中国农村多是自己纺纱织布。即便有了“洋布”,穷苦人仍是穿自己织的“土布”,不似现在,人人都能穿上丝绸、涤纶、纤维的布料。
苦难亦不能阻隔人的美好愿望,于是有了针尖上的夏布绣。夏布绣以手工夏布为面料,采用巧手加针法,以心中的愿景为题材,以梦幻般的构图,借助夏布的自然纹理,将心中所想绣在夏布上,虽然粗糙,却也古朴典雅。从根脉上追溯,夏布绣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中华刺绣。
张小红着青绿色绣花斜衣襟上衣,下身穿以绣点缀的黑色直筒裤,低盘发,皮肤白皙,文静雅致,从外貌和气质上无法断定她的年纪。她读书不多,却谈吐不凡。
张小红做得一手好女红。女红是女人的艺术。中国古代评价女子就两个标准,一是相貌,二是女红。张小红的女红不是随母亲学的,也不是婆婆教的,而是姑婆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四五岁时,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心思全在工厂里。母亲是公社妇女主任,整天在农村跑,家长里短的事她都管,就是没时间管张小红。外公心疼她,把她接到身边,张罗她吃喝。这时,她生命中一个重要女人出现了。外公让她喊“姑婆”。姑婆面容姣好,手拿一方绣花手帕。
小红歪着脑袋问:“姑婆是谁?”
女人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说:“姑婆就是你妈妈的姑姑。”小红眼睛盯上了绣花手帕,伸手去摸那朵花。
女人惨淡一笑,问:“想学绣花吗?学好了才能嫁个如意郎君。”
小红问:“姑婆嫁了如意郎君吗?”
女人说:“姑婆不嫁。红红长大了要嫁。”
小红噘着嘴说:“姑婆不嫁,我也不嫁。”
农村天大地大,张小红原是跟着一群男孩子玩,成了假小子。自从认识姑婆后,转性了,安静乖巧地蹲在姑婆身边,看姑婆把七彩丝线绣进头巾,绣进鞋面,绣进四四方方的小围兜。看得多了,她便跃跃欲试。外公宠她,鼓励她说,真是我陡岗的娃!
张小红娘家是瑞昌。瑞昌坊间说,无户不剪纸,无女不绣花。陡岗是瑞昌的一个偏僻乡镇,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剪纸绣花。外公拿出麻布边角料让她玩。张小红这一玩便痴迷上了刺绣。姑婆没等到出嫁,二十岁便去世了。姑婆是痨病,干不得重活。姑婆走之前绣的莲花鞋面、鸳鸯枕套、百子被罩却是为她而绣。
后来,张小红的父母支援三线,调到原9394厂,举家迁往新余,她便离开了瑞昌。
地缘是人心中的河流,不管人走到哪都在汩汩流淌。张小红似乎冥冥中在按照姑婆的安排,嫁人生子。刺绣是为了嫁好人,不是做女人唯一的追求。丈夫来自匡庐秀峰脚下,是一个农家娃。两人是厂里的同事,夫妻和睦。然而,生活的压力让他们越来越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