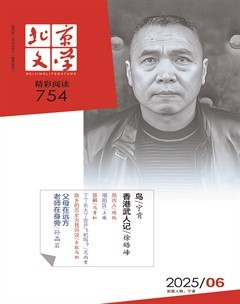1
寂静的午后,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过来。
“林林,你在哪里,我在厚街。” 三姨问道。听着她亲切的声音,我顿时睡意全消。
黄昏时分,我驱车抵达厚街的一个城中村。两年未见,三姨消瘦了许多。她依旧是那么热情,早已做好一大桌子热气腾腾的菜。
三姨在东莞给表弟带孩子。这是个一室一厅的房子,三姨带着孩子睡卧室,表弟和表弟媳睡在客厅那张锈迹斑斑的铁架床上。
我忽然被房间一隅的几个刚编织好的竹篮深深吸引。“没事无聊做着玩的。”三姨笑着说道,嘴角边荡漾出两个酒窝。
墙角的竹篮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那些与竹子有关的点点滴滴迅疾浮现在脑海里。
1990年深冬的一天,三姨从紧挨火车站的东里村嫁到龙源村。六岁的我跟在送亲的队伍后面,走了一上午,终于把三姨送到三十里外的山旮旯里。群山环绕的村庄,一条坑坑洼洼的泥路通进村子。送亲的队伍吃完酒席,歇息片刻,开始返程。我跟着母亲沿着山路慢慢往回走,走出好远,回头张望,依旧看见三姨站在山头目送我们。我踮起脚尖使劲朝三姨挥手。母亲眼角溢出一滴泪,她跟三姨感情深,未出嫁时,她们一起拔猪草、做农活,形影不离。
三姨是干农活的好手。在那山旮旯里,她每年种七八亩粮食、两亩西瓜,养一百多只鸭子、五头猪、两头大黄牛,紧挨着房子的后山上散养着五十多只鸡。
夏天,屋后的山峦还笼罩在一片晨雾中时,三姨起来了,推开大门,扯开嗓子朝寂静的山谷吆喝一声,沉睡的山谷似乎被她喊醒了,几分钟后,隐约听见树梢传来的阵阵清脆的鸟鸣声。就着昨晚的剩菜吃了一碗稀饭,掩上门,三姨就出发了。她吃力地拉着一板车西瓜上坡,过陡坡,路平了就好走。从山里到小镇的集上,有二十多里路。波浪起伏的山路暗喻着她一生的艰辛。
拉着一板车西瓜到镇上,天已经完全亮了,她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湿透。卖完西瓜回到家已是午后,她通常饿得肚子咕咕直叫。
四个姨妈中,我和哥哥最喜欢去三姨家。沿着长长的柏油马路一直走,左拐,越过山坳,是一片寂静的竹林,一阵风袭来,竹叶哗哗作响。一小片一小片竹的新绿汇集在一起,变成绿的海洋。竹林里弥漫着一股清幽的凉意,穿过竹林,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前面那片密集的坟墓让我胆战心惊。哥哥大喊一声跑,我迈开步子迅疾奔跑起来,风在耳边嗖嗖飞过。穿过那片密集的坟地,眼前豁然开朗,踮起脚尖,就能隐约看见三姨家的房子。
晚上,昏黄的烛光下,我们几个安静地写作业,屋外山风呼啸。山风裹着整栋房子,屋内却温暖如春,偶尔有一丝风透过窗的缝隙跑进来,在房间游弋,烛火微微摇曳。三姨在一旁做着针线活,她细长的身影映照在墙,随着摇曳的烛火晃动着。静谧的屋子里,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
三姨家屋子后面是一片广阔的竹林。
记忆中那个深夜,雨水敲窗发出密集的响声,一道锯齿形的闪电划破夜空,转瞬消失在苍茫的夜里。借着闪电的亮光,我清晰地看见翠绿的竹子在风雨中左右摇摆,我静躺在床,倾听窗外的雨声。
夜色越来越深,雨势时缓时急。一觉醒来,远处的山峦青翠欲滴。
太阳缓缓升起,晨雾慢慢散去。
隔壁屋子响起一阵窸窣的响声,是三姨起来了。一夜的狂风暴雨,竹林里弥漫着血腥的味道。一些竹子在风雨中折断。
我们在清晨的竹林里游荡着,很快就摘满了两大竹篮鲜笋。竹筏漂浮在岸边,一阵晨风吹来,竹筏微微荡漾,惊起阵阵涟漪。三姨撑着竹筏,载着我们,把新鲜的竹笋运到对岸十里路外的圩上卖。
晨雾笼罩着河流,上岸后,把竹筏拴在水边的树干上,三姨挑着两竹篮竹笋匆匆往圩上赶去。我们紧跟其后,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裤脚。
2
在故乡那条小路上走了大半生的三姨,此刻在异乡的这条路上来回走着。从出租屋通往幼儿园的路,她已来回走了三年。
三姨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竹子。竹子仿佛一座无形的桥把她的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让她有了依附感。
那天,把孙女乐乐送到幼儿园返回出租屋的路上,三姨看到一家竹器店,细长的竹子重重叠叠堆放着。枯黄里泛着些许青色的竹子映入眼底,勾起了她的回忆。她在这里带娃三年,每天从这条路上路过,却没看见这家竹器店。
回到出租房收拾好家务,在窗户下的板凳上坐下来,竹子的那抹绿又浮现在三姨的脑海里。她起身,锁上门,疾步来到竹器店,买下了三根细长的竹子,又折身去附近的五金店里买了劈刀和柴刀。看着这些熟悉的工具,与竹有关的往事顿时涌上心头。
拿起工具,她依旧十分娴熟,干枯的记忆顿时变得潮湿起来。
几天下来,接送孩子做家务之余,她利用空闲的时间编织出来两个竹篮子。竹篮结实耐用,外观也很精致。
她把两个竹篮拿到附近的菜市场去卖。守了一个上午,终于换来五十块钱。她紧捏着这五十元,像是捏着自己生命的根须。乐乐没上幼儿园前,她的时间捆绑在乐乐身上,每天带着她漫无目的地在出租屋附近的公园溜达,直至脚板走得酸痛了才返回。上幼儿园后,每天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她大都孤坐在床沿盯着那台冒着雪花点的二手电视机打发时间。时常看着看着她就睡着了,电视机依旧开着,声音回荡在窄小的房间里,透过窗户满溢到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