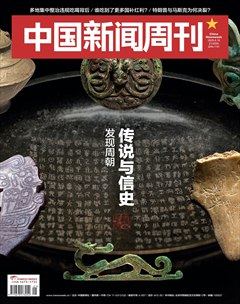“师傅,这单我只付了8元,送我这么远,你能愿意吗?”
贵阳网约车司机韦波照常出车的一天,一名乘客上车后轻声问他,带着些许“担忧”。这一单要跑约10公里,韦波听得出来,乘客第一次用这个平台打车。他解释,自己能挣13元,如果对方没有新用户补贴,这单的付费价格应在14—15元。这一单看起来双方都很“划算”:乘客用很低的客单价打车,会员司机仅被平台抽佣1%—10%,首充会员甚至只抽佣1元。
近期,一家名为“小拉出行”的平台正用这样的策略吸引司机运力和乘客订单,向客单价1.8—2元/公里、抽佣比例25%—30%的头部平台发起挑战。
小拉出行成立于2021年6月,是由货拉拉内部孵化出来的一个创业团队,自成立起脱离货拉拉独立运营。平台此前多年未能打响知名度,最近喊出了“网约车界的拼多多”的口号,来势汹汹。
截至今年5月,其客运业务已拓展至全国10个省、56座城市,以二、三线城市为主;顺风车业务则已布局261座城市。
但“低价”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为乘客提供便宜出行服务,怎样兼顾服务质量?面对更低的客单价,司机能挣到更多钱吗?在长期固化、“内卷”的网约车行业,小拉出行杀出一条血路的可能性大吗?
瞄准二、三线城市
每天早晨7点,韦波准时出车。他住在贵州最大的小区花果园社区,第一单往往就从这里开始。
“一个网约车司机得有2—3部手机。尤其在很偏的位置,滴滴打开,高德打开,小拉打开,都是必需的。”作为一名有6年经验的网约车司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
早高峰不缺订单。如果他选择打开的是小拉出行,在“抢单大厅”界面,可以直接看到附近的订单,显示出距离、接驾时间、总里程和价格信息。“大部分都是去大十字、小十字(贵阳著名商业中心)的办公大楼,或者世贸广场上班的。我想好自己早上去哪个区办事,就抢去那边的订单。”
“抢单”是小拉出行的特色,司机选中心仪的订单后就要点击订单下方的按钮。接下来则会出现“10+人正在PK中!”的弹窗,随后揭晓抢单结果,抢到了便出发。
另一种选择是打开其他头部网约车平台,接受平台派单。“早高峰时期,由于贵阳的地域限制多,山多,隧道多,岔路口和高架都容易堵车,可能半个小时原地不动。”韦波进一步解释。事实上,由于小拉出行遵循“一口价”模式,堵车的情况下收入不变,滴滴等平台则会对应涨价,他在高峰期仍然主要跑滴滴,到了平峰期就转而使用小拉出行。
据韦波回忆,小拉出行2021年就进入了贵阳市场,当时,高德、曹操、首汽、T3等网约车品牌纷纷涌现,“滴滴的订单渐渐被瓜分”,做了2年滴滴司机的他也开始观察新事物。在小拉出行的“低价”攻势下,平台订单不停在增多,“身为老百姓,大家都想选便宜的”。他开始两个平台混着跑,这一习惯延续至今。
“网约车出行尚未在国内所有城市普及,当前仍然呈分布不均的态势。”国际智能运载科技协会秘书长张翔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面临网约车运力过剩的问题,司机收入下降,行业需要精简;而在缺乏运力的二、三线城市,新平台仍能为当地的出行需求提供有效补充。
“贵阳等二、三线城市的优势在于,该类城市城区面积小,供需密度较高;待挖掘的潜在用户数量基础较大,市场有空间;收入相对于一、二线城市较低,生活节奏略慢,也有更高比例的人群会对价格敏感。”小拉出行相关业务负责人刘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也正因此,贵阳逐渐成为小拉出行“最香”的市场之一。在订单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司机选择加入。除此之外,多位受访司机表示,另一项重要原因在于“接单自由”,可以自主选择订单。
“自动派单的平台经常会让司机接单后从市中心开到偏远小山村,而回来的二三十公里路程却始终是空放,现在我可以直接不选。”韦波说,另外,由于订单价格便宜,和乘客有更多商量的余地,“对方都比较客气,有时候我想途经某个点快速办个事,大多会答应。而在自动派单的平台,稍微一绕路可能就被判处违规,限制较重”。
遵义司机郑万里从2023年开始逐渐从滴滴转移至小拉,他表示,一方面,遵义居民在小拉出行下的出城单、回程订单更多;另一方面,小拉出行可以让他选择出发点距离更近的订单,在高峰期有挑选订单的机会,避开拥堵的城区。
“在其他平台,我也经常同乘客对账,扣除平台抽佣、车辆和油费成本,收入比订单价格少了1/3。现在,每个月缴纳399元会员费,但仅有1%—10%的抽佣比例,整体算下来很划算。”他说。
在小拉出行早期“野蛮生长”阶段,平台曾因合规问题受到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