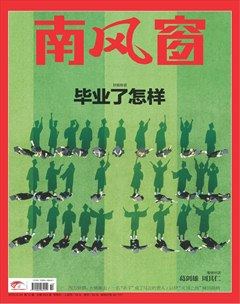县城“婆罗门”群体凭借地缘人脉资源,与在城市打拼却难以融入的“精英”形成鲜明反差,这种结构性矛盾,如何加剧了社会心理失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有9 亿多,其中4 亿多人离土离乡,即便常年生活在城市,仍死死攥紧农村成员权,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土地收益预期与对未来的想象?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小县大城》作者周立,早年深耕金融领域,却因深感这一领域悬浮无根,转而将研究目光投向广袤乡土,进而关注到“小县域、大城关”的县域发展样态。
随着城镇化率突破67%,“乡土中国”的静态图景早已被“城乡中国”的动态格局取代,土地收入在农民家庭账本里也已退居二线。长期被忽视的县域群体,正是发展的主力军。
小县城的大价值
南风窗:你在《小县大城》一书中提出“小县大城”的概念,最初是什么契机使你关注到中国县域发展的独特性?
周立:贪大求全,常常是国人心态。小的,难道没有价值,不够美丽?最初,我主要从“小与大”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考与切入。小人物与小县城的价值常被忽视,城市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人们往往认为城镇化只有“大国大城”一条路径。但近期在重庆的两场演讲,让我深受触动。有一次直播现场,15 万听众中,竟然近90% 的人来自县城或县域,这让我意识到县域群体的普遍性与重要性。
真正促使我深入研究的,是在福建德化的调研发现。我和罗建章博士在德化看到一组惊人数据,其城镇化率与森林覆盖率均达78%,近80% 的人口集中在县城居住工作,这种“人口集聚与生态保护并存”的模式在全国县域中极为少见。更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化虽导致农村人口外流,但人去屋空的背后,是县乡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当地绿化水平同步提升,乡村更让人向往了,这印证了 “小县大城”与“绿水青山”的潜在关联。
南风窗:怎么理解“小县”与“大城”这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它与“大国大城”的路径又有什么关联?
周立:第一是从狭义的人口角度来看,“小县城、大城关”,意为进入县城人口多,城镇化率随之提高;第二是从广义的发展角度来看,“小县城、大发展”,县城虽小,但能够有类似大城市的发展效率;第三是隐含的线索,即“小县城、大中国”,通过县城能看到中国的面貌,以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可能走向。
“小县大城”并非个案,全国至少十多个省区,如湖南、江西、贵州、广东等南方丘陵山区,已推出类似战略,有的明确提出“小县大城”概念,有的通过“大城关聚集”等制度安排,推动县域发展。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美国30%以上人口仍生活在乡村,德国八成以上人口居住在5万人以下的聚落形态中,而中国城镇化率虽然只是67%,但对照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欧美和日韩,人口已经高度集中。其中常被忽略的县城,作为连接城乡的关键节点,其价值和功能亟待被重新认识—它并非与“大国大城”排斥对立,而是共生互补。
南风窗: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这个过程中,农民与土地和村庄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周立: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三大核心特征—农民生产的土地粘着、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社会生活的终老是乡,这曾是21世纪之前,千年中国社会的典型写照。但当前的情况是,中国城镇人口已超过乡村,“乡土中国” 的静态结构已被打破,进入21世纪的中国,已演变为“城乡中国”。
这种转型可以被拆分成前半程和后半程来理解:前半程以人口离乡为特征,农民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等方式融入城市;后半程则强调城乡对等,如第一代农民工因年龄和家庭因素开始返乡养老,而第二、第三代农民工的去留则取决于在城市的扎根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