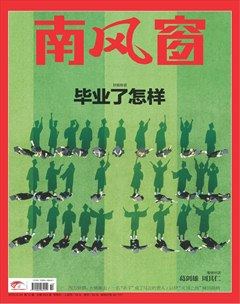这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在一栋十几层的大写字楼里,它几乎相当于一个单人公寓。麻雀虽小,维持公司运转的不同功能却都完备:上下两层的loft式装修,下层是产品展示台、员工的办公工位,上层划分出好几个区域,分别用来制作产品、直播和拍摄。房间门外,一块风格古典的木质门牌上写着这个小工作室的名字:映竹。
20岁的邹文君是公司的CEO,她同时也是一名大三学生。她创立的知君竹传媒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品牌营销,而“映竹”则是她今年新成立的自己的水晶饰品品牌。目前,公司已经和200多家品牌方达成合作,每年的流水大约有50万。
像邹文君这样的大学生CEO,正在变得稀有。接受采访的大学生创业者都提到,自己几乎是同龄学生群体里唯一一个创业的人。邹文君大一就开始创业,曾想过在校内找学生创办的广告公司合作项目,但没能找到,“在上三届和下三届,基本上创业的人只有我一个”。
与近年来持续的“考研热”“考公热”相反,创业对于大学生而言较为小众。而热潮之外,这些刚刚毕业就踏上创业道路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做出如此选择?在他们眼中,创业意味着什么?
来自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创业者回答了这些问题。创业之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成年后的“第一桶金”,更关乎如何成长,以及成长的前路。
探问人生
走上创业的道路之前,邹文君并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学生”。
她学习成绩并不好。中考后,她考进珠海市的一所重点高中,学习压力大,她又有些偏科,和同学之间的差距很快显现出来。她的成绩跟不上,心理落差很大,“别人家的小孩怎么都这么厉害?”
在大家都很“卷”的环境里,她选择了“躺”。那时候,大多数同班同学都非常刻苦。邹文君记得,距离高考还有五六个月,午休期间,室友会在寝室里背单词、写作业,甚至有人不回宿舍,整个中午都在教室学习。每天晚上十点寝室熄灯后,室友们同样会在寝室里学习。
同一时间,邹文君会偷偷打开手电筒,在床上读书。这些书和高考无关,她喜欢读名人传记:比如毛泽东、张居正,还有各个朝代的皇帝。她常常看书看到凌晨两三点,室友也学习到凌晨两三点。
“躺平”的背后也存在着焦虑。每次出成绩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明显,“真是完了”,她一面和同学开玩笑说自己考不上大学了,一面又想,还是得考个大学。
更大的焦虑来自目标感的缺失。“因为你跟你周边的人想的不是一个东西,大家都在想学习,但你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像对这东西不是很感兴趣,怎么办?”
而恰恰是这种痛苦,催促着年轻人追问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怀揣着这个问题,他们开始走出既定的轨道,开始自己的尝试与探索。
高中时的邹文君对此思考了很多。父母的人生道路给了她参考。她的父母学历都不高,父亲年轻时白手起家创业开餐饮店,现在已经开成了连锁店,而母亲在企业内的工作能力也很强。她读高中的时候,母亲在一家企业做HR,筛选简历时把一沓简历剔除了出去,她还向邹文君解释,这一沓简历的求职者学历背景好,但没有经验,而针对这个岗位,他们更需要有经验的人。
“当时我想,比起考上某一个大学,更重要的是考上大学之后要做什么。”过往阅读的名人传记,还有父母的经验,都在告诉邹文君,大学之外,她还能探索更广阔的人生图景。
差不多同一阶段,Kiwi也在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向他抛出这个问题的是语文课本里的史铁生—这个长期困于残疾的作家,在《我与地坛》里写下自己的人生感悟:死亡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既然死亡这一终点已经确定,没有确定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
“当时我想,比起考上某一个大学,更重要的是考上大学之后要做什么。”过往阅读的名人传记,还有父母的经验,都在告诉邹文君,大学之外,她还能探索更广阔的人生图景。
史铁生的感悟,给高中的Kiwi带去很大的触动。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他开始了自己的探索。那也是他最早的“创业”。
他开了一个自媒体视频账号,运营一个月左右,就能收获两三万的播放量。视频内容主要是文学作品解读,其中就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花了很多时间,查找相关的研究论文、历史资料,尽量把这篇文章拆解、分析得更为详细和深入,最终的视频也有上下两个部分,合计大约二三十分钟。
他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触动分享给更多的高中学生。他们曾经和他一样,困于课本,却没有时间去思考课本里的深意。后来,Kiwi的期待也收到了回音:有一些高中生在他的视频下留言说,他们的老师会在课堂上播放这个视频,或是把它当成作业,让学生们课后观看。
创作与发布视频,本身也是他的自我追问。而现在,这种追问影响了更多的人,这次小小的“创业”让Kiwi感到意义非凡。
尝试只是一个开端,真正的创业还需要经验与时间的积累,而在摸索与痛苦中,踏入创业道路的机会才会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