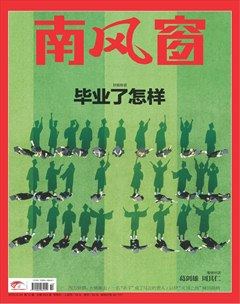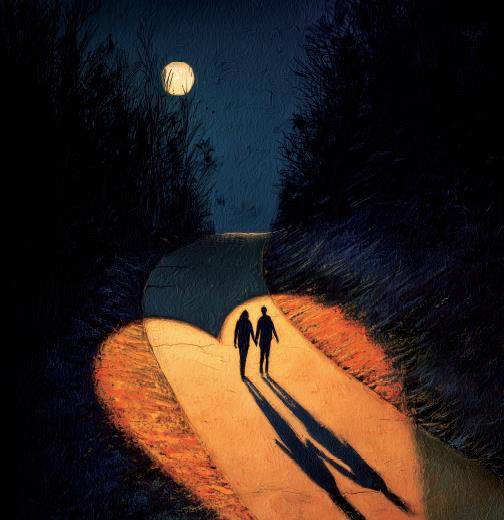
联系上陈仪与陈辰的时候,他们正在筹划回陈仪的老家办婚宴。十年前,我在大学里刚认识他们时,他们还未在一起。但2015年的夏天过去,他们的恋情就已经扩散到一部分同学们之间—这是我当年想象中校园爱情的模样:在偶遇、绯闻和只有两人知道的小欢喜里,火花细微地绽放,无私地分享。
从“校园”到“婚纱”的复古爱情,几乎已经在这个时代绝迹了。即便校园爱情仍然能保持某种值得铭记的纯粹,现实高墙的撞击也让普通人更加难以承受。
今年夏天,24岁的研究生于霄和同龄的莫昕,分别被自己谈了4年的恋爱对象分手了。于霄,是因为女友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莫昕,是由于双方工作后的作息与目标太不一致,在无法磨合的矛盾下,不得不选择放弃这段感情。
从学校到社会,人被外部世界的变化分隔,作为一种与他人、与世界、与自己相处的平衡艺术,期望爱情的持续变成了一种奢求。在就业环境变得复杂的今天,学生时代爱情的无疾而终更加容易受到理解。
更大的视野里,一代人的恋爱观念都在发生变化。现实与理性很多时候超越了浪漫与激情,主导着人们的爱情选择。投入身心去爱在十余年前还被视为勇士,如今却成为小丑。
如今,在以“05后”为主力军的大学校园里,爱情的重要程度排位并不占前列。2021年,《中国青年网》一则面向全国13979名大学生的恋爱调查显示:近七成大学生单身,超五成大学生无恋爱经历。
即便是在成年后,也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去恋爱。但人们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窥视与研究,正如北大硕士、脱口秀演员鸟鸟描述的,大学里的恋爱现状是:“有爱情的人体验爱情,没有爱情的人研究爱情。”
而在复杂的现实议题面前,学生时代最宝贵的财富是青春。青春与爱情之间碰撞出的独特火花,一去不复返。它也许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落地成通往幸福的坚实桥梁,也许跟随青春逝去,变成学生时代那朵照亮世界后悄然融化的雪花。
我们当然也听说过那样的故事—走出校园大门,由于人生规划的截然不同,或者回归到自己原有的被家庭、社会期待拉扯的框架里,两个人不得不分道扬镳。
婚姻或分手,都不必然意味着爱情的结局。真正值得铭记的,是在明确感受到爱情的那些瞬间。
不谈爱情
校园里的爱情很少因为条件匹配而相合,大部分情况下,暧昧先在友情的基础上萌芽。
学校建在山上,需要走过长长的下坡路。月亮悬在天上,两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然后触碰到一起。
陈仪与陈辰都是在香港念本科的内地学生,他们专业相同,恰好姓氏也相同,两人的许多课程都被排在一起,座位也挨得近,一来二去渐渐成了朋友。他们发现,两人都爱看球,最喜欢的球队也是同一支。
有一年冬天,陈辰的手冻破了,陈仪给了他一支护手霜。根据她的说法,本意是“借”给他用的,陈辰却以为是送给自己的。第二天,陈仪没等到护手霜的归还,却等到了陈辰送的一支唇膏。
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在同一个图书馆巧合偶遇,然后很有默契地,第二天再次在同一个地方相会。有时,两人不会说话,只是安静地自习,结束后再一起走回各自的宿舍。
学校建在山上,需要走过长长的下坡路。月亮悬在天上,两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然后触碰到一起。
确认关系的一年后,大三上学期,陈辰出国交换。异国的半年,陈仪时不时在朋友圈里刷到陈辰发的一张仅她可见的照片,都是她以前没见过的自己的照片,配上一段小诗。断断续续发了快一年,直到两人再度相见。
二十出头的年纪,爱情更容易受到微小养分的浇灌而萌芽。如今,陈仪回想起来,这段感情能顺风顺水地走下去,得益于“不过度期待”。她善于发现二人之间相似而非相异的地方,也善于珍藏那些微小的付出和幸福。
比如现在,两人一起在香港生活。每天早上出门上班前,陈辰会顺手煮早餐,提前看天气,然后叮嘱陈仪带伞。而让陈辰感动的是,他随手在短视频里分享过的某种食物,陈仪真的会花心思找到这样一家餐厅,在他生日的时候带他去吃。
也许学生时代的爱情之所以能轻盈,经得起怀念,恰是因为不必过早面对现实。相对确定的情境,相似的生活节奏,以及皆处于较小物质负担的阶段,让情愫更容易附着于一些微小的片刻而鲜活起来。
上海一所“985”大学的研究生吴优认为,自己与前任长达四年的感情,主要归因于两人都心照不宣地“不谈爱情”。
2018年夏天,大一学生吴优在社团里认识了当时暂时作为指导老师的博士生周舟。上课没有麦克风,大声说话很费嗓子,吴优就带去龙角散。社团有两个老师,但她只给了周舟。

两人顺理成章地加了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