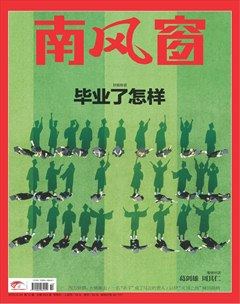gap year的中文译为“间隔年”,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后流行于欧美国家,是指学生完成高中或大学学业后,按下暂停键、跳出既定的升学轨道,去旅行、实习、做义工、学习新技能或探索兴趣的一段时间,通常为期一年。
如今,这个概念正在被中国年轻人广泛接纳。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网络上表达着对gap year的向往,渴望在节奏紧密、不容停歇的升学压力中得到喘息。
社交媒体常把gap year描述成一款针对当下生活困境的“万灵解药”:跳出轨道、奔向旷野,在看似缤纷的生活图景中,一切烦恼都灰飞烟灭,自此从社会规训中得以解脱。
与之一体两面的是,gap year又常被叙述为一种脱轨的失控、落后的恐惧、再次回归主流秩序所面临的阻力—似乎向gap year迈出一步,就意味着万劫不复。
特别是当应聘时,企业对gap year有负面的反馈。而这类消息总是被大规模地转发和放大,最终被人们总结成一句短小精悍的流行语:“中国人不配拥有gap year。”事实真的如此吗?
怎么在快毕业时被压垮了
2024年夏天,本科毕业后,了了选择开启自己的gap year,朋友纷纷表达了羡慕:“真好!我没有gap的勇气。”
但了了决定去gap,却是因为大三末的一次崩溃。
那是2023年5月,她拨通父母的电话,大哭了一场。这让父母有些错愕:女儿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住校,成绩优异,个性独立,不用人操心,一路顺风顺水,考入985大学,怎么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突然被压垮了?
在电话中,了了告诉他们,自己决定推迟对研究生项目的申请,毕业后先休息一年。生活在广东小城市的父母,出于对女儿状态的担忧,无措地应允下来。
导致了了崩溃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彼时,她正在北京和朋友策划一次当代艺术展,那是她“第一次走进所谓的成人世界”。然而,一方面,因经验匮乏,她始终惶恐不安。
另一方面,她在现场认识了一群同样入围策展的朋友,朋友们对策展极其专业、充满了激情。和他们待在一起,了了感到些许迷茫:“大家都有了明确的职业目标,我也快毕业了,为什么我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同时,有一门科目的考试时间与策展时间冲突了,导致了了收到了下学期补考重修的通知。这件事严重打击了她作为好学生的自尊心。
再加上,此时距离海外院校研究生项目的申请截止日期,只剩下五个多月。完美主义作祟之下,她迟迟无法完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作品集。所有的负面情绪积压在一起,让了了心中始终绷紧的弦,忽然断了。
大学头三年,朋友们一致评价她像个“机器人”。朋友们习惯了她经常不知踪迹、杳无音信,知道她一定是全身心投入在结课作业、竞赛项目之中,通宵达旦。
大学头两年,她的志向是保研,大三开始转向留学。她把既定的大目标拆分成每学期、每门课,甚至每一天的任务指标,然后有条不紊、逐个击破。
就像机器人一般稳定“运行”了三年,在那个暮春,了了缓过神来—生活是高密度的、规律的、已知的、可能通往所谓“成功”的,但她忽然再也找不到继续下去的理由。
决定gap之后,她建了一个收藏夹,收集其他人在平台上分享的gap生活,起名叫“野人计划”。这份“野人计划”中,有在川西原野上打手碟的青年,有西园寺的师傅身边围绕着飞舞的鸽子,有从广州出发去拉萨的火车全程53个小时,还有很多人在世界各地旅行打工。
决定gap之后,她建了一个收藏夹,收集其他人在平台上分享的gap生活,起名叫“野人计划”。
“电子屏幕里的世界好美,不如让我亲自去看看吧。”她写道。
2025年6月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柯柯,则是在去年夏天迎来秩序垮塌。
她在山东一所一本大学就读会计专业,专业是自己选的,当初觉得“好就业、能赚钱”。然而到了大二,她便发现,无穷无尽的数据对自己来说是如此枯燥乏味。她考虑过是否要转专业。她喜欢小动物,有过“转去学与宠物相关的专业”的念头,但这个念头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不喜欢所在专业是一种常态。柯柯对南风窗说,她同班同学中,“九成都不喜欢学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