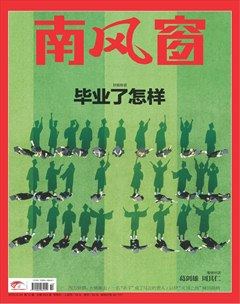葛剑雄教授今年80 岁了,这位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曾经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如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精力充沛。6月13 日这天,从下午到晚上,他有两场媒体专访和一场在书店举行的活动,始终未现倦色。
我问他在身体和精力方面感觉如何,他说没有问题,还在做着正常的工作,一天两三场甚至感到“轻松得很”。他说,自己的观点是不要主动迎合衰老,认为到了某个年纪就不能做某些事情,是不正确的,反而会衰老得快。
史学者张宏杰是葛剑雄的学生,他在文章《我的老师葛剑雄》里,叙述葛老师的三个突出特点,第一个就是超乎常人的精力充沛和勤奋。他是不用手机的,只用邮箱联系,密集活动的午餐间隙不休息,在飞机或高铁上,更是不休息,而是在工作,在谈话,在写作。
因此,他留下了如此多的文字。今年新出版的两本文集收录了他过去十年间的文章,通览下来,不得不感叹他的经历之丰富,涉猎之广泛。与人们通常对学者终日苦坐书斋的想象完全不同,他喜欢东奔西走,自述三个月走进非洲,三个月往南极科考,两个月重走玄奘路,所去之地,远至北极点,高登乞力马扎罗山,而与此同时,他写作、主持编写的文字,怕有上千万字之多。
他曾在2008—2018 年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成员,与国家相关决策部门和国家领导人多有接触,所以看他的文字,同他交谈,能够感受到他的位置角色所赋予他的言说方式,与其他并不具有如此身份的历史学者的区别。或许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常被人称为敢讲话的“葛大炮”,另一方面,又容易引起同一拨人的非议。几年前,他正因为一番在他看来颇为正常的讲话而引起民间学者的批评。
以我的观察来看,葛剑雄教授并没有变,在这次采访中,曾经引起讨论的话,他仍然如常地反复言说。在别人看来会矛盾的地方,他处理得成熟而坦然。或许,他们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批评者想象的那么大。现实的决策和选择并非历史学家所做,作为历史学家,葛教授完全同意并坚持表达的是,首先要尊重历史、研究真相、普及常识,在这一前提下,决策者才有可能做出积极的、明智的选择。
研究真实的历史
南风窗:今年出版的两本文集收录了你过去10 年的文章,现在回顾,你是什么感受?
葛剑雄:2014、2015 年, 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集,有7 卷,内容是我70 岁以前的,这次出了两卷续集,收录了我70 岁到80 岁之间的文章。
我写的序言、前言、后记、书评较多,所以编写了第九卷《也是读书》。我认为,为他人撰写序言,前提是也要认真阅读,这些也是读书的产物,所以用了这个名称。
第八卷是《何以中国》,这一卷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地理、丝绸之路、长江黄河、运河等等,并非专著。这里面也收了一篇我以前编的秦汉史教材,它是作为大学里面的选修教材使用,公众通常看不到这些内容,所以我把它放进去。还有一篇是我给科学出版社2023 年出版的《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写的总序《何以中国》,里面的内容可以涵盖这本书,我就把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
大部分文章是前几年写的,有一篇《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历史地理学的使命》是交稿以后再补进去的,我认为这篇比较重要。
南风窗:近年中国人对何为中国以及身份认同的问题越来越在意,有些人看到某些形象和表达,会认为这不应该是代表中国的形象,是对自己的侮辱。你一生都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这些年你对什么是中国有新的思考吗?
葛剑雄:如何理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这里面有不同方面。重要的是史实,需要通过考古、分析文献才能知道。作为历史学者,我的任务首先是恢复历史真相。可惜现在对许多常识,大家的认识都并不准确。所以我这些年做的事,是尽量纠正学术界和广大公众对所谓常识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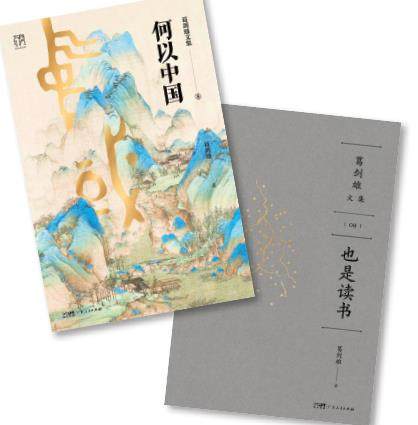
例如,我发现大家对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误解很深,充满夸张,甚至根本不了解这段历史。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才提出来的,而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很片面。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也不是原来有的,是到1968 年日本人(三杉隆敏)提出来的。中国古代很少有过主动的外贸,有的多是走私。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时,认为自己的资源足够,不需要外面的东西,是别人需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