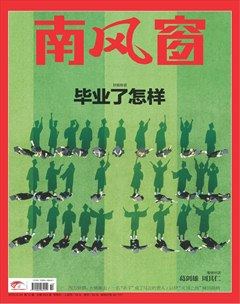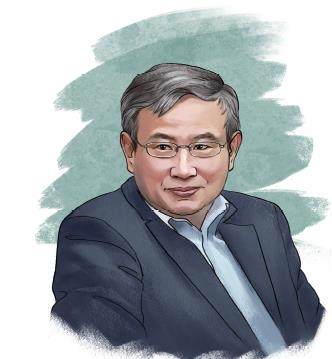
一开始,周其仁并不那么愿意跟我们聊“调查研究”的问题。
因为他总觉得,它不适合被单独讨论。调查研究是科学方法,是认知世界的整个过程中的一环,在整体中跟其他环节互动,而非孤立。
2005年,南风窗启动了“调研中国”项目,每年资助数十支大学生团队走向田野,展开调查。18年前,周其仁曾指导北京大学的学生团队对宿迁医改进行调研。今年5月,我们联系到周其仁,有关“一位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何应该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讨论,他仍然是最适合的访谈对象。
周其仁曾在北大荒当了10年知青,其间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近10年在“农研室”,盐水里泡,沸水里滚,用脚步丈量中国农村土地上的变化,周其仁重视实证和经验的学术风格基本形成。
1989年到1991年,周其仁到英美访问学习,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转向专研土地制度问题和乡镇企业发展。在他的著作《城乡中国》里,开篇他说:“中国很大。不过我们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城市,另一块叫乡村。”
他多年研究,就在这两块地方之间来来回回,从未停止。
南风窗与周其仁约定在北京金融街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他对单独谈论调查研究方法的抗议,本就是对社会调查研究的一种评论。采访结束,他匆忙离去,第二天,他又要出差。
他的实践,在为他的思想作注脚。
调研需要方法,也需要结论
南风窗:多年经济学研究,你坚持了社会调研和实证研究这条路子,为什么?
周其仁:社会科学,希望自己“成为科学”。这个“科学”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人类用自然科学的方式认识世界,社会科学试图向它靠,但是到今天还是有距离。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做实验,但实验是可控的,把复杂的影响因素抽掉之后,去看它的规律。这个方法,在研究人在社会当中的活动时,却难以适用,因为谁也不能造出一个可控的社会。所以我提出“真实世界经济学”,意在追问,面对一个“不纯净”的真实世界,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要怎样去调整。
在脑子里做实验,把现象抽象成概念,概念之间进行推理,形成某些命题—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这样产生的,所以经济学好像看起来最像科学,满篇都是数学符号,但是如果没有可控实验,这些看似精密的推论其实是无的放矢。
但人的活动是能提供经验教训的。我们去调查研究,“调查”就是看发生了什么,“研究”是分析里面的问题。老是争论就不能做事情,我们就需要方法,也需要结论。改革开放一开始划定经济特区,特区实际上就是做实验,厦门汕头深圳珠海,各自的结果不一样。
在实验结果上,我们又没有定论,因为自然科学的实验过程是公开的,谁有争议,把这个实验做一次就好了。但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实验是不能复制的,这就导致很多事实的争论,会演变成政治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我们必须加强调查研究。第一,制定政策的时候会谨慎一点;第二,能增加更多做对事情的机会;第三,帮助你总结教训。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不依靠调查研究,那就是唯心论,比如宗教占主导,中世纪的愚昧就是这样,(欧洲国家)到自然科学革命之后才意识到人可以利用理性改善生活,社会科学也慢慢发展起来。但总体上看,它还是落在自然科学的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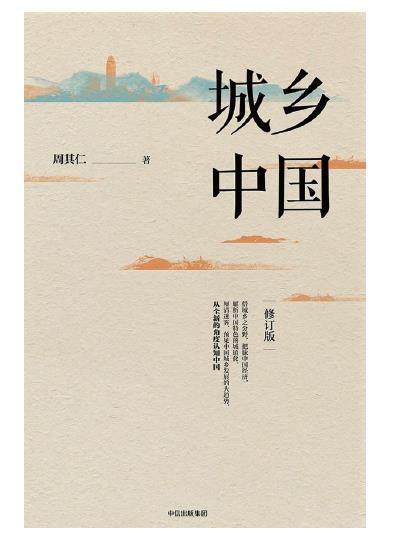
南风窗:经验很重要,但是只依靠经验,是否也有问题?
周其仁:有人看到一只乌鸦是黑的,第二只也是黑的,第三只也是黑的,其他人来报告,说河南看到的乌鸦也是黑的,所以得出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结论可靠吗?只要遇到一只白乌鸦,他的结论就会被推翻。这就是经验主义下的认知惯性,接受不了例外,甚至把它打成假的,实际上,如果你知道有些乌鸦是白的,你对世界的认知就进步了。
经验主义下的认知惯性,接受不了例外,甚至把它打成假的,实际上,如果你知道有些乌鸦是白的,你对世界的认知就进步了。
所以人要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经验,经验之外要有理性思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