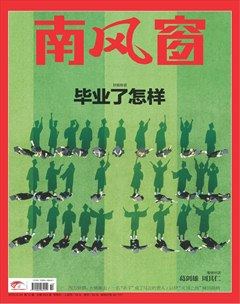直男导演怎样拍好女性题材?
2023年,秦天的首部长片作品《但愿人长久》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单元获得最佳剧情长片的荣誉。之后,不少人对导演、编剧秦天有这样的好奇。
2025年6月,《但愿人长久》在院线上映,南风窗跟秦天有过一次采访。跟之前的设想大为相悖,这并不是一个聚焦于女性主义的采访,但这跟秦天的想法却一致。他从未想到从女性主义出发来创作,他只想讲述城市化进程里真实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历史,只不过他选择的是女性视角。
故事从一个叫夏婵的女性出发。她出生在一个知青家庭,有个妹妹叫夏娟。贫困年代里,她不得不早早辍学挣钱,供妹妹读书,这造成她多年委屈。电影开始时,她先后遭遇诈骗、失业,怀着身孕而不知道人生该往何处。多年后,她在夜总会陪酒挣来自己在成都立身的资本,努力争取给女儿尔思更好的生活。这时,她的外甥女小芒从老家来到成都投奔她,打破了她的平衡,但也给了她一个机会与过去和解。
采访那天,我们提到,与秦天的创作同时期,另一位青年导演祝紫嫣也拍了一部名叫《但愿人长久》的电影。更加巧合的是,这两部电影都在讲代际和亲情。采访那天,我跟秦天说,我觉得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到了一个时代的节点,在相似的感受下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动作,就是去回望我的祖辈和父辈,它像是一种时代情绪。这个撞名的巧合,反而在电影之外给这两部作品带来更复杂更丰富的意味,它本身就是创作者跟时代连接的产物。
导演秦天如同在抢救一代人的历史,重现着一代人的心结。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人抓住有限的东西活下去,人与人之间结下密密麻麻的疙瘩,然而正因如此,我们被绑得更近。
以下是秦天的讲述。
迁徙的人
最开始,我并不是想要拍一部女性电影。这部电影,主题是迁徙的人。
上中学之前,我的生活都处在一个非常固化的环境里。我出生在成都,长大在成都。少年时期的我,曾一度以为自己非常了解世界,上大学之后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我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
我在成都的一所大学学经济,那是2003年,我的很多同学来学习这个专业,是抱着改变命运的想法。2007年毕业,之后的六七年时间里,他们完成了资源和财富的积累,在城市里落了脚,成了家。
与城市化进程步调一致的个人奋斗故事,提醒了我: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生活之外。这时候我心中有一点默默的自惭形秽,过去的十几年我在干吗?我好像只是一直顺着一个被规定好的路径走,封闭的环境把我改造得一点毛边都没有。
所以毕业之后,我拒绝了进入金融机构工作的机会。我大概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一种强大的、模式化的、反复的、准确的工作,它会支配我,异化我,给我一种优渥但是被规定好的生活,作为我服从这个体系的许诺。
我对人性—至少是对我自己的那部分人性,有充分的了解。如果我轻松拿到这样的薪水,让我天天坐在透明的柜台后面做同样的工作,我想我可能就“出不来”了。
不相信我能出来,我就先不要进去。人是很容易被控制的,我想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自由”。
但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所以在此后的十年里,我做了很多零散的工作。
它们的共性是门槛很低,很容易申请。比如医疗销售,电脑销售,少儿机构的托管老师,小区游泳池的救生员,网球陪练。我还帮人经营烧烤店,自己开过“野的”,这是成都的说法,就是黑车司机。有阵我还来到北京,在中关村混迹了一些时日。
我主动让自己经历着这种短距离的迁徙,在一种人为的漂泊当中,我确实在一点点离粗粝和真实更近,它们隐形、失声,但却大量、广泛。其实我才属于这个社会的少数,当然,对社会的了解让我知道,还有比我更“少数”的人存在。
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生活之外。这时候我心中有一点默默的自惭形秽,过去的十几年我在干吗?我好像只是一直顺着一个被规定好的路径走,封闭的环境把我改造得一点毛边都没有。
做这些工作,给我带来了不可计量的生命经验。开“野的”时,有次我送一个大学生去双流机场,返程是空车,觉得有点亏。出机场不远我路过一个公交车站,看到一个穿校服的中学生拎着箱子孤零零地等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