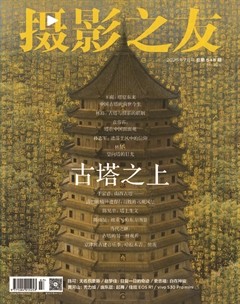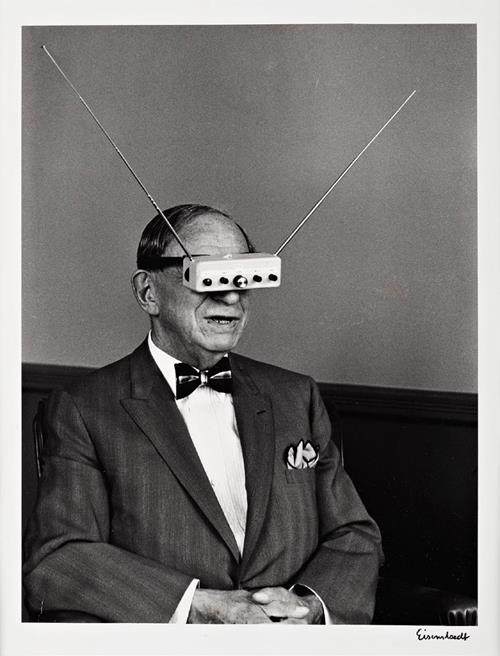
摄影在当下的普及,已经成为大众娱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如果你真正喜欢摄影,要警惕的正是:切莫让摄影成为没有思想的游戏。
孙郁在《游戏之于思想》中曾经做过对比,将鲁迅与梅兰芳作为可以互为参照的不断生长的遗产,并非对立的存在。他认为,在京剧里,人物是类型化的,故事再曲折,结局都以大团圆为主。而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等人翻译的易卜生戏剧,给国人的印象,一是写实的力量,将生活中隐秘的存在托出,让人有彻骨的体味;二是打破了平衡感,确立了个人主义精神。胡适曾肯定尼采式的精神,要做偶像的破坏者。他自己的气质,虽然与尼采相去甚远,但就思想方式而言,尼采与易卜生都给了他不小的启示。他的审美思想与传统戏剧的距离,是一下子可以看出来的。传统戏剧让人有悠然的欣赏感受,而现代艺术则显示存在的无序,并引入思索的险境中。因此,写实的艺术不是对观众的催眠,而是精神的冒险,引入惊涛骇浪中,于是也打开了思想之门。
鲁迅的审美理念也是如此。不是亲和观、寻找彼此的平衡,相反,而是冒犯观众,以残酷的拷问撕裂视觉的帷幕,告诉人们一个荒唐的存在。鲁迅笔下的世界是灰暗和沉重的,他不仅不讨好生活,也不讨好读者。他欣赏的是大漠惊沙,深渊里的死火,以及无路之途的孤魂野鬼。但在绝望里,依然有精神的热力。就鲁迅、郁达夫等作家而言,人性有复杂的图景,不能以脸谱的方式简单为之。所以就会在这些新文学家那里,看到了反本质主义和忧虑,以及个体意识的韧性。
孙郁总结说:中国艺术不缺乏游戏之乐,缺乏的是思想。没有思想的游戏,总还是单薄的。
这样的单薄,在中国摄影中也比比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游戏之乐,根深蒂固于中国人的创作理念中,自然也难逃摄影人的利用。于是当我们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游戏之乐的影像中陶醉的时候,摄影的力量也就全然“躺平”了。
这里不妨来看一组生活工作于伦敦的艺术家和讲师的安斯沃斯的作品。和他另外的一系列作品一样,主要探索客体的有机和无机状态,以及和人类的关联。他曾涉猎那些往往被人类忽略的建筑和空间形态,位于都市的边缘地带,然而又和都市休戚相关。作品曾获各类奖项,并有个展在伦敦展出。而“覆盖”则是一组如同身体形态的系列作品,描绘的是摄影家父亲花园中包裹的棕榈树,为了抵御冬日的霜寒。这一系列作品完成于春天伊始,也就是抵御冬日严寒的保护解除之前。画面如同游戏般诡异,却蕴含了独特的思想因子。正如玛丽·霍洛克曾说:“当代花园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定性,部分冲突,部分协和:是神秘的愉悦和尘世的不完美的结合。”
这类家庭的花园是一种人为控制的非自然的空间,经常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中。这既是对自然空间的探寻,同时又是人类欲望持续发酵的象征,让自然屈服于人类的意志。通过摄影演绎这样的主题,主要是让观众有一个想象的空间,无法预料覆盖物之下是什么。因为在照片中棕榈树变成了雕塑,覆盖物的褶皱如同是水母或者蘑菇云,抑或有嘴有鼻有眼的人性,却是匿名和静默的形态。这些从地面上长出的形态又如同生根般地伫立在一个底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