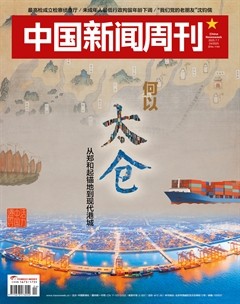救护车800公里收费2.8万元,究竟贵还是不贵?
今年4月,江西唐先生的孩子患有重症,通过一家民营医院即南昌赣医医院的救护车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运至上海一家医院,800公里的路程收费2.8万元,唐先生质疑其是“黑救护车”。6月18日,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报,证实南昌赣医医院存在收费不合理等问题。
不过,该通报发布后,一部分网友提出,800公里路途遥远,途中还使用了ECMO设备,2.8万元的收费并非完全不合理。尽管这一事件中的救护车是不是“黑救护车”仍存在争议,但这一事件使更多人开始关注“黑救护车”。
“黑救护车”不是新现象。当前,120急救体系仅覆盖危急重症,这导致非急救转运需求转向民营机构,也就因此出现了缺乏资质、胡乱收费的“黑救护车”。
“黑救护车”为何屡禁难绝?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原主任武秀昆长期关注“黑救护车”现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出现“黑救护车”现象的原因错综复杂,主要原因是合理的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统一的非急救医疗转运体系,让非急救医疗转运市场健康、科学、有序发展。
“‘黑救护车’小卡片装了好几个纸箱”
陈欣没想到,送病重外公从医院回家的短短3公里、10分钟路程,要花费1800元。
2024年8月,80多岁的外公已经在广东湛江一家医院住院将近两个月,患有心脏病、肿瘤等多种疾病,某天晚上突然全身冒汗,经抢救后身体仍持续恶化,直到几天后失去意识。“当时我们决定带他回家,于是联系科室主任,希望能安排救护车,对方说医院救护车不能送这种病人回家,但给了我们一个私人救护车的电话。”
陈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救护车一到,对方就开价2000元,“我舅舅和他说1000元行不行,对方说不行,最后谈到了1500元。回家之后,把我外公抬到屋里,对方拿出收款二维码,又提出要1800元,我舅舅没有心情和他争,就付了钱”。救护车上一共有三人,除了司机,一人穿白大褂,一人穿便服,“但是穿白大褂的人没有提供任何医护服务,只是坐在车上”。此外,救护车里只有一张移动床和氧气袋,没有其他医疗设备。
武秀昆曾围绕非急救医疗转运发表过几十篇文章,他总结,“黑救护车”有两大基本特征,即低成本投入和低成本运营。“黑救护车”的随车医疗设备通常因陋就简,甚至使用陈旧报废的设备以次充好,或者设备压根不能正常使用。另外,绝大多数“黑救护车”都没有医护人员随行,或者随车人员没有执业资质,“只是穿一件白大褂而已”。
正因为车上没有靠谱的随车医疗设备,“黑救护车”的危害也显而易见。《中国新闻周刊》查询裁判文书网发现,近几年,多地都出现了患者与医院和“黑救护车”之间的民事案件,涉及健康权、身体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2024年长春中级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2020年,一名叫刘丽丽的女子因患风湿病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医生未对她进行药物过敏、药物适应证和禁忌证方面的风险评估,给头孢类抗生素过敏的刘丽丽注射了头孢吡肟。两天后,医生告知刘丽丽母亲,刘丽丽需要到北京进行救治,随后刘丽丽被假冒“吉大一院”的救护车转往北京,途中,刘丽丽母亲发现救护车上的医生不是“吉大一院”的医生,车辆也不具备起码急救条件,连氧气瓶都不够用。当救护车行驶到北京时,刘丽丽在车上去世。
当前,“黑救护车”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一位应急医疗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20年之前,他曾受国家相关部门委托,带队在全国10个省份开展“黑救护车”暗访,后因新冠疫情暴发而中断,最终暗访了7个省份、几十座地级市、上百家医院和急救中心,“省会城市全去了,每个省份至少去了4座城市,每座城市基本会去大学附属医院、人民医院、中心医院等”。
经过暗访,他们发现,大量医院门口都有“黑救护车”,医院的病房里,甚至医生和护士办公室里总能看到各种“黑救护车”的小卡片,“最后我们收集的各地‘黑救护车’小卡片装了好几个纸箱”。
广东民航医疗快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航医疗快线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国内首家由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机构,该公司董事长陈仲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十几年前,广州的“黑救护车”通常都由面包车改装,拉人就看“谁的拳头大”,乱象层出。现在,“黑救护车”大都有救护车的外观,挂着外地车牌,长期停在医院门口,甚至还有救护车冒充民航医疗快线公司,“打着我们的旗号,名片上印着我们的logo,写的是自己的私人电话,患者根本没办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