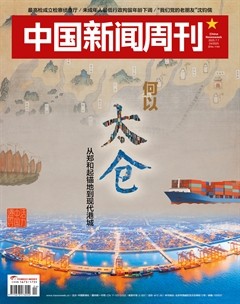6月27日下午4点才过,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社总编陈丽杰正忙着手上急务,同事叫她:“蔡澜先生走了!”陈丽杰心头一紧,想起最后一次见面,还是2019年,后来经历疫情,再后来蔡澜因骨折住院,俩人没能再见,但陈丽杰还时常关注着蔡澜的微博,俩人偶在微博私信中联络。
83岁的蔡澜还沿袭着10年前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在微博上与合作伙伴及友人沟通,也在微博上分享日常,他的分享于今年3月归于沉寂。4月时,香港媒体说他进了ICU,助理登录他的账号报平安:“老毛病休息一下就好。”他自己也很快更新内容说:“未至病危,请不必担心,一笑。”但此后,他的身影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一同隐去的,还有那个属于“香港四大才子”的风云时代。
世人眼中的蔡澜,是“香港四大才子”中最为洒脱不羁的一位将“游戏人生”四字演绎得淋漓尽致。金庸对蔡澜的评价有三:一是潇洒快活;二是见识广博;第三点尤为有意思,说黄色笑话时听起来只觉得好笑而不觉得猥亵。多年后,许知远亦在节目里感叹:“至少在我目力所及处,蔡澜先生,算是最懂得享受人生的人了。”
他好像没留下什么传世之作,但是名字前面的定语不少,作家、电影制片人、美食家、旅行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电视节目主持人、“蔡澜点心”创始人……很多人去他开的“蔡澜点心”吃过饭,还有人被他指点过迷津——他连续10年在微博开展“迎新年活动”,和网友在评论区聊天,大概算最早的情感博主。有人说,想跳出舒适区。他问:为何?有人问:坚持一件事付出却没有回报怎么办?他回答:算啦。微博上曾有个热门话题,叫“人生松弛感挑战”,有人说,没人比得过蔡澜。
2025年6月27日下午,蔡澜的亲友在他账号公布讣闻,蔡澜于6月25日去世,公布时蔡澜遗体已被火化,遵照他的意愿,为免叨扰亲朋,不设任何仪式。
这个潇洒一生的侠士,拂身而去。
“蔡澜”像“菜篮”,注定吃喝一生
蔡澜自小在新加坡长大,父母为避战乱从汕头下南洋,全家住在“大世界”游乐场内,推窗就是喧闹红尘。小时候叛逆,讨厌作业,讨厌学校,蔡澜没少转学,母亲叹他“如野马,无校可关”。父亲蔡文玄是新加坡一家戏院的经理,同时也负责邵氏电影公司的部分宣传工作。从小在戏院长大的蔡澜曾经一度认定电影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那时他最高纪录一天看六部电影,中间吃点零食充饥,把城市中放映的戏都看干净为止。散场后与伙伴游荡至天明。“那是天堂。”他后来写道,因为有电影,有荒唐,有未耗尽的青春。
14岁那年,他干了两件轰动的“大事”。在《星洲日报》发表影评《疯人院》,稿费全换了街边肉骨茶宴请同学;又用笔名痛批父亲发表在报上的诗作“是什么屁诗”,气得父亲摔了茶杯,却不知作者是谁。
作为爱电影的人,他赶上了好时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战后日本电影的黄金期。被同学称为“电影字典”的蔡澜选择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刚好邵氏在日本的经理准备退休,看着蔡澜长大的邵逸夫对他寄予厚望:“你可以接任。”蔡澜于是半工半读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主要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到香港放映、宣传和发行等工作。那一年,蔡澜才16岁。后来有记者问他:“那么年轻,心里有一些忐忑吗?”蔡澜回答:“也没有,那时还年轻,就想着人家叫你做,好啊!”
大学毕业,22岁的蔡澜被邵逸夫召回邵氏,抵港任监制和制片经理。20世纪80年代,进入香港电影黄金期,《城市猎人》《福星高照》《龙兄虎弟》等风靡亚洲的商业电影中,“监制:蔡澜”的标记十分常见,其中的《龙兄虎弟》让成龙一飞冲天。
成龙回忆:“很多年前,当我和洪金宝、元彪一起在欧洲拍戏的时候,我们身边有个人,教给我们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