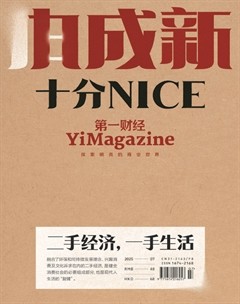湘湖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里,躺着一艘独木舟的残骸。
据讲解员介绍,这艘八千年独木舟的特别之处,是国内第一次挖掘出古人类使用石锛等新石器工具在一棵硕大的马尾松上“刳木为舟”,并且还创造性地使用了火焦法。
5月,夏浅胜春,风暖昼长。我们杭州湾南岸区域两岸考察团一行来到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我们考察的首站。跨湖桥所在的湘湖地处三江交汇处,与西湖隔江相望,是浙东古运河的孕育之地。
博物馆的外观被设计成一条巨船,掩映在古湘湖芦苇荡里,不远处是石桥、宝塔,古意盎然。所谓跨湖桥,是因为我们所在的这片地方,即古湘湖的上湘湖和下湘湖之间,横跨一座桥。2002年这里的砖瓦厂采掘湖底淤泥,才让文物得以重见天日。事实上,明清以来湘湖周围窑所林立,它们都觊觎湖底厚达四米的优质淤泥—那是制陶烧砖的好材料。也正因此,和独木舟一同出土的,还有138件制作精良的施彩陶钵,上面镂刻着令人惊叹的太阳纹、天梯纹和八卦数字。

尽管“越人操舟若神”,相对于熟悉的农耕文明,我们对古人在海洋文明上的表现依然知之甚少。第四纪更新世末期以来,自然界经历了3次地理环境沧海桑田的剧烈变迁,其中卷转虫海侵在距今70 0 0年至60 0 0年到达高峰以后,宁绍平原沦为一片浅海,古越族先民在海面上升的过程中与大自然抗争,同时逐步南迁或流散,其间产生了跨湖桥、河姆渡等文化遗址。
博物馆一隅,陈列了一堆古越人的麻栎果(也叫中国橡子),这是我的老家金华—从浦阳江回溯两百公里的浙中山区—的人过去经常食用的一种淀粉类果实。这得是保留了多久的食物传统……,我们吃的那些麻栎的种子,说不定就是在海侵后那些南迁的越人带给我们的。上个世纪末,我的乡人还经常在现在这个季节上山采果,晒干磨成粉后做成可口的砟子豆腐,放凉后加入砂糖和食醋,用以消夏。一篇科学文章认为,在古越人划独木舟的时代,类似麻栎果这样的野生坚果可能更适合我们的祖先,因为它的热量回报率是那些虽然已经驯化但结实率较低的粳稻的2到6倍1。


相对而言,在北宋政和二年即1112年,一位名叫杨时的官员来萧山当县令时,水稻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当时的人口激增,而且已经吃上了外来的占城稻,但农民苦于没有水来灌溉农田。了解到百姓强烈的筑湖愿望后,杨时不畏困难和阻力,决定筑土为塘。经一年多的艰辛,3.7万余亩的新湖建成,灌溉了周边14万余亩田地。这片新湖,就是今天的湘湖。
很多人知道“程门立雪”这个求学典故,但未必知晓故事里那位孜孜求学的程门弟子,就是这位倾听农民心声的筑湖官员杨时。而800年后,当一个叫陶行知的人来到湘湖松竹繁茂的定山推行他的乡教大计时,他也曾向当时几个在山脚下锄地的农民请教是否可以协助建校办学,就像一个城里人向乡下人讨教如何种菜一样。
西兴
“烟波尽处一点白,应是西陵古驿台。”这是白居易笔下的西兴驿。西兴古镇是全长250多公里的浙东古运河起源之地,由此出发,古运河途经绍兴、上虞、余姚、宁波,在镇海城南注入东海。
在西兴老街,萧山本地摄影师佳杰带我们去吃运河土菜馆,说那家的霉豆腐最地道。菜馆的边上,便是过塘行陈列馆。
所谓过塘行,是帮客户管理货物的地方。“七月三十日,晴。晨至西兴,落俞天德行。”有关西兴和过塘行,绍兴周作人曾专门属文《西兴渡江》,一一介绍在过塘行如何吃饭、上渡船、帮船家摇橹等出行规矩。

在陈列馆边上一张复原的官河过塘行名目表上,我找到了周作人提及的“俞天德行”。“过塘行的隔壁或对门,照例是一家小饭店……”,过塘行的隔壁果然是一家叫傅合兴的饭店,就在妆亭的边上。那座一看就是后建的妆亭,传说是春秋时期西施在此梳妆、待诏入吴的所在。
在西兴美术馆,我们邂逅了来自法国的飞行教练、航海爱好者冯克礼先生。老冯正和中国朋友一起用现代技术和材料恢复一艘宋代古船,备战年底的帆船大赛。在他位于运河边、如船舱般狭小的房子里,挂着几张红帆船照片—它们来自他的家乡,法国北部的布列塔尼。19世纪,布列塔尼的渔民发现用松树皮中的单宁酸鞣制棉质帆布,可以防止船帆发霉。正是这种单宁,让帆布呈现出浓郁的日落红,并很快传到美国东海岸。

建于明万历的永兴闸距离老冯的住所也就几十米的距离,比我想象的要袖珍很多,却一直忠实地履行排涝引灌、阻挡海潮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