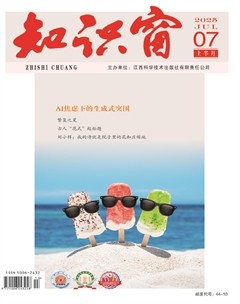2025年3月初,方大同因病去世,年仅41岁。看到这条消息时,我一时难以平静。
方大同的歌未必陪伴了我整个青春,但在我的青春里多次响起。如今,我仍处于青年阶段,那一颗太阳还在轰轰烈烈地往最高的穹庐处攀登,怎么在来时的路上,已经有一段风景再也进不了春天?
罹患恶疾、英年早逝,在这两个词语的反衬下,“诗酒趁年华”这几个字无比醒目地占据了我的脑海。
曾经,我以为身体是一座潜力无穷的宝藏。不管怎样压榨,它休息一段时间,总能恢复过来。读大学时,我的入睡时间从晚上十一点推迟到十二点,再推迟到凌晨一点半。我心里总想着,第二天多喝点咖啡,就又能精神奕奕,于是一次次试探,一次次得寸进尺。工作后,周末无休、通宵、喝酒应酬轮番上阵,打得我落花流水。灵魂即使当局者迷,也清楚地感受到了身体各处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信号。
精力真的能像息壤一样用之不竭吗?如果一切都有上限,用一点就少一点,那么年轻时就把余额透支完,老了之后用什么?会不会在清零的那一刻,就是我的灵魂与这副身体租约解除的时候?
晚上吹头发时,我忽然看到几根白发躲在黑发里偷偷瞅着自己。十年前,我会觉得染一头银发又帅又时髦,现在,白色成了不怀好意的不速之客——年轮还没有给它报幕,怎么就提前登场了,还没到它为身体衰老拉开序幕的时候!我想起王维的《叹白发》:“我年一何长,鬓发日已白。俯仰天地间,能为几时客。”人世匆匆,在主人家端茶送客之前,我这个世界的过客,还能待上多久?不知道,但幸好,茶水还在袅袅地冒着热气,我也还有太多的东西想听主人家聊起。比如气蒸云梦泽的洞庭湖怎样波撼岳阳城,比如让韩愈吓得“乃作遗书,发狂恸哭”的华山是何等险峻,比如让李白惊叹从天上而来的黄河有多壮阔……
咦,我竟攒下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心愿。那我之前在做什么?哦,在等。等着退休了,再用一双并不利索的腿脚奔赴祖国的大好河山,为脑海里一张张便利贴挨个打上钩。于是,从燕子斜等到了梅花斜,从陌上花开等到了独钓寒江,未来,还要再等上无数个日升月落、寒来暑往。可是,心愿并不会为我停留。莫高窟的壁画不断被氧化,月牙泉难以维持粼粼的波光,九寨沟被地震摧残得伤痕累累……“还没好好地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许多地方的冬天已经不下雪了。当我终于能背上行囊时,有多少心愿会像古莲子一般,早已无法发芽,只能成为某种纪念,封存在回忆的博物馆里?
有人曾问,究竟是怎样的远大前程值得我们把四季都错过?有人回答:“我没有获得四季,也没有赢得远大前程。”当人对雨后的泥土、天际的彩虹和晨光里的鸟鸣都变得迟钝,只对闹钟保持居高不下的敏感度,算不算是对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身体的背叛?难怪一些古人难以想象的病症探出了头。日复一日,我们忙得天昏地暗,可在回首时,总是隐隐有种一事无成的荒诞感。在名字散成一缕袅袅云烟前,我们为它打包了哪些能带走的行李?风吹来时,它真的会露出心满意足、无怨无悔的微笑吗?
求学时,试卷中会出现这些作文题:“慢慢走,欣赏啊;过程比结果重要;低头走路,抬头看路……”可惜,踏入社会后,我记住的是如何一语双关、点到为止、言有尽而意无穷,却忘了我曾经是如何言之凿凿地论述人要满怀热忱地活在当下,并在物欲横流中守护灵魂的丰盈、清醒、诗意和自由。
方大同曾翻唱《红豆》:“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在《特别的人》里,他又唱道:“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几回细水长流。”如今,物是人非,我再听这两首歌,思绪开始翻飞。往后余生,我不仅仅要去珍惜,更要趁早拥有天长地久;不仅仅要让年少时的书生意气细水长流,更要让大水漫灌的生命细水长流。
诗酒趁年华,了无遗憾后,安享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