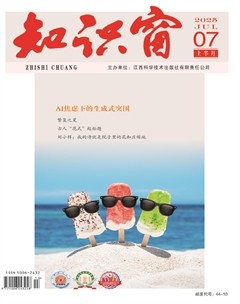AI焦虑下的生成式突围
窗外的梧桐叶簌簌作响,我在凌晨三点的台灯下反复修改着策划案。电脑右下角突然弹出新闻推送:“某大厂裁员30%,AI模型接管基础岗位。”光标在屏幕上明灭不定,仿佛某种隐喻。这个场景,或许正是当代职场人的集体写照。当机器学习的浪潮裹挟着代码与算法汹涌而来,我们既惊叹于它重塑世界的伟力,又惶恐于被拍碎在数字沙滩上的宿命。
2024年深秋,我所在的公司引入智能办公系统的那天,部门里最资深的平面设计师李姐对着自动生成的上百张海报沉默良久。那些精准匹配用户偏好的设计稿,每一幅都像在嘲笑人类设计师的迟钝。午休时,我听见她在茶水间低声叹息:“学了20年美术,最后要给AI当校对员。”玻璃幕墙外,城市的天际线在数据流中明暗交错,恰如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的技术裂变。
这种焦虑源于认知的断层。当深圳市福田区的数字员工能在秒级生成执法文书;当在特定病灶的CT影像识别中,医疗AI的阅片准确率超越三甲医院的医师,传统经验构筑的职业壁垒正在数字化浪潮中分崩离析。就像19世纪的纺织工人面对蒸汽机的轰鸣,我们站在智能时代的门槛前,突然发现那些引以为傲的手艺,不过是机器眼中可复制的代码片段。
但焦虑的深层机制,实则是人类对自身价值的终极追问。某夜翻阅《人类简史》,尤瓦尔·赫拉利关于“无用阶级”的预言令我脊背发凉。当AI不仅能模仿凡·高的笔触绘制新作,而且开始理解《蒙娜丽莎》微笑里的哲学沉思时,我们是否终将沦为技术的附庸?这种恐惧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发酵成铺天盖地的“AI速成班”广告,那些承诺“三个月转型为AI工程师”的课程,像极了溺水者抓住的浮木。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知识窗》2025年7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