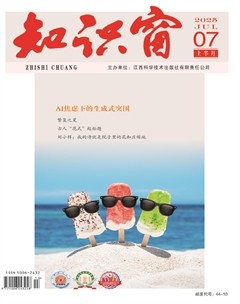故土有“耳”
早年,依河而居,每一场春雨总会给人惊喜。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当轰隆隆的雷声犹如龙吟一般从大河上空滚过时,大雨哗啦啦地下了一夜。翌日雨霁,一轮红日从波光粼粼的河面升起,河声、鸟鸣、蛙唱、牛哞、羊咩,合奏成这个春天特有的交响曲。
当路过一片草坡时,我忽然尖叫了起来。只见草地上躺着湿漉漉、软绵绵的东西,有些像木耳。它们仿佛从地上长出来的褐绿色的耳朵,静静地趴在芨芨草、牛筋草、狗尾草等草丛间,一直延伸到河滩,有些竟爬到河滩的石头上,仿佛在凝听、传递、暗示什么。
“这是地耳,是雨水馈赠的野蔬,在荒年,它可是救命菜。要不,咱俩捡一些回家尝尝?”父亲见我好奇,征求我的意见。我欣然同意,于是父亲放下柳筐,脱下褂子,弯下腰和我一起捡地耳。
地耳嫩滑,黏糊糊的,倘若一不小心,就会从指间溜掉,“哧溜——”落入草丛里,很费工夫。见父亲一拈一个准,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将五指张开,罩在地耳上方,五指一齐探向它的底部,然后慢慢合拢,飞快提起,将它摊放在小褂上。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知识窗》2025年7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