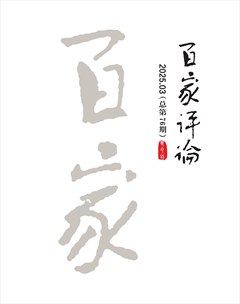内容提要:刘知侠在短篇小说《红嫂》中将“乳汁救伤员”的民间本事置于宏大的革命历史叙述结构,在讲述红嫂侠义事迹的同时,呈现出一幅“军爱民、民拥军”的革命史诗画卷。文本中人物所展现出的“快意恩仇”的侠义伦理,在阶级话语的规训下被置换为“为人民献身”的集体信仰,实现了革命话语对“侠义精神”的符号化改造与收编。小说借助戏曲、影视等跨媒介传播,使“红嫂”形象逐渐演变为大众文化中的革命侠义图腾,实现了意识形态教化与民间审美传统的有机融合。《红嫂》对侠文化的征用并非简单的政治迎合,而是在叙事、伦理、媒介的三重互动中,完成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为理解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文化逻辑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1961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的《红嫂》,是刘知侠创作的一部歌颂沂蒙山区劳动妇女的不朽篇章,堪称“写一部有关沂蒙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书”①的承诺所结出的精神硕果,更是革命文学中为数不多的讴歌女性的经典文本,它延续了作者创作的一贯风格。1954年,刘知侠的首部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小说以高昂的革命激情讲述了鲁南地区的铁路工人打击日寇、破坏敌人交通线的传奇故事,为我们塑造了一群拥有顽强意志和英勇战斗精神的男性侠义英雄形象。而在《红嫂》中,刘知侠密切关注曾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却鲜少被提及的女性形象,将宏大的革命历史与普通劳动者的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深入挖掘战争时期普通劳动者的英雄事迹及其面对战争的精神心理,讲述了沂蒙地区的普通劳动妇女红嫂在危急关头抛却思想枷锁,大胆地敞开胸怀用“乳汁”救助受伤战士的感人事迹,展现了她在现实革命斗争中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无私奉献的巾帼豪情和侠义气度,成功塑造了劳动妇女英雄的典型形象,使其成为革命文学女性形象谱系中的“这一个”。
在既往研究成果中,有研究者从小说改编的京剧《红嫂》入手,认为“它生动地体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那种鱼水深情”°,塑造了红嫂这样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农村妇女”③,奠定了《红嫂》跨媒介研究的基调。随着小说的跨媒介传播及其影响力的扩大,部分学者开始挖掘“红嫂”原型,引发了“红嫂”究竟是谁的争议,一般认为是沂南县的聋哑妇女明德英。还有不少研究成果从劳动叙事、女性主义、红嫂精神与沂蒙精神的关系等层面对《红嫂》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它们推动了《红嫂》研究的深入发展。但大多流于文本层面的解读及本事的探源,而对本事背后蕴含的民间话语及其与革命信仰关系的发掘有欠深入。
基于此,本文从“本事一故事”的叙事嬉变、侠义伦理的政治美学转化及跨媒介传播等层面对《红嫂》进行重新观照,深入探讨小说对传统侠文化的革命性重构,揭示革命话语对传统侠义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力图为重新审视红色经典作品的价值意蕴提供一种新的维度。
一、从“本事”到“故事”:侠义符号的双重演绎
在侠文化的精神谱系中,“本事”与“故事”之间的叙事张力是构成其鲜活生命力的双重源泉。从《史记·游侠列传》的本事实录到唐传奇的故事演绎,从宋元话本的市井书写到当代红色经典的意识形态建构,侠文化游走于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之间,不断形塑和丰富其精神内核。沂蒙地区身处齐鲁大地,历史上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汇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兼容道、法、墨、阴阳等诸家思想在内的文化守成主义、民间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等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思想体系。°这些思想的相互杂糅,推动了仁义礼信、伸张正义、快意恩仇、言出必行、义薄云天等文化质素的形成和演进,潜移默化地浸润和滋养着沂蒙地区广大民众文化心理和精神人格的养成与构型。几千年来,生活于沂蒙大地上的无数仁人志士养成了伸张正义、豪气干云、勇于担当的侠义品格,前仆后继,演绎着一曲曲威武雄壮的生命壮歌。“侠是一种有良知、血性和正义感的舍己为人、激扬生命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唯侠独有,是人之为侠的本质特征,其中的义是侠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的价值核心”?。小说主人公红嫂是沂蒙大地的女儿,以此为价值标尺来看其“乳汁救伤员”的行为,堪称一位女侠的义举。然而,“从民间‘侠’文化的角度来看,齐鲁之‘侠’主要不是‘以武犯禁’,而是一种社会正统秩序被破坏后的补救方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当沂蒙地区的生存规则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时,胸怀民族大义和民间正义的人们被时代大潮推向历史的前沿,“红嫂”作为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受难者和战争的亲历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地支持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事业,其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由此衍生。
小说《红嫂》创作之际,正值新中国文艺强调“革命历史叙事”的重要时期。历史记忆和革命话语相结合的文学创作既是对当时政治任务的积极回应,也是对革命伦理的艺术化呈现,更是文学与时代的深度互动。这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问世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红嫂热”,也引发了寻找“红嫂”本事的热潮。所谓本事,分为人物本事、事件本事和情境本事三种类型,是指原本的或原生态的事实,“限定在作家所历、闻并参考的原本之事上,假如一件事实作家从来不曾知晓,那么尽管它真实存在,也不在本文所论‘本事’范围之内”。随着对“红嫂”人物本事的深入溯源,研究者们挖掘出一批沂蒙山区普通劳动妇女的感人事迹,有乳汗救伤员的明德英、藏匿战士的祖秀莲、养育革命英雄后代的张淑贞…那么,到底谁才是刘知侠笔下的“红嫂”呢?
最初,沂水县桃棵子村的祖秀莲被认为是刘知侠作品《红嫂》中的人物本事,这源于文本中“红嫂在秫秸垛里看到了一个负伤的解放军同志”①,而祖秀莲藏匿战士的空间正是秫秸垛。据《临沂百年大事记》载,祖秀莲与明德英都曾救助过受伤战士,前者曾将郭伍士藏在高粱秸垛中,后者则将伤员搁置在空坟中,因此,两人都被誉为沂蒙“红嫂”。“秫秸垛”和“空坟”这两处空间地点最开始被视为溯源人物本事的依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红嫂的人物本事渐渐浮出水面。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一般认为“红嫂”的人物原型是沂南县的聋哑妇女明德英,她曾多次义无反顾地救助八路军战士。第一次,在坟场用乳汁救活了一位被敌人追杀的小战士,战士痊愈后重返抗战前线;第二次,明德英的丈夫带回十三岁的庄新民,她再次将战士视如亲子、尽心尽力。?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看,其创作激情源于李子超“乳汁救伤员”的叙事话语,而明德英的事迹与此话语基本吻合。因此,“乳汁救伤员”的情节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事件,也是溯源“红嫂”人物本事和事件本事不可或缺的符号。
“乳汁”是演绎“红嫂”侠义精神的具象之物。在小说文本中,“乳汁”多次被提及:由最初“她迅速地打开了衣襟,把上身向彭林的头部俯下去…阳光从秫秸垛的隙缝里透射进来,它照着红嫂的脸,她的面孔上的红云褪去了,现在显得那么庄严、神圣和崇高”的模糊呈现到“在端去的米汤里,偷偷地挤上一些奶汁,来增强彭林的营养”再到“奶水本来就不多,现在要分给两个人吃,这怎么够吃呢”以及“红嫂把奶头向孩子的小嘴塞进、拔出,拔出又塞进,反复好几次”等。③作者将红嫂的救人行为纳入了“人民战争”的宏大叙事框架,通过描写红嫂的义勇行为和崇高精神及食不果腹的苦难处境,建构起红嫂“乳汁救伤员”的政治美学。一方面,红嫂“乳汁救战士”的侠义之举,体现了民间伦理的“侧隐之心”;另一方面,红嫂哺育战士的行为是“哺育革命火种”的象征,响应了“要革命,就得有牺牲”的革命号召。因此,“乳汁”从生理意义上的食粮逐渐升华为“革命圣血”的符号及“生命源泉”的象征,暗示着红嫂精神由民间侠义行为到革命集体信仰的政治美学转化。
在本事与故事之间的转化与互动中,作者根据创作的需要,在丰富的本事材料里选取了最能激起情感共鸣的“乳汁救伤员”情节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将民间伦理叙事和革命战争叙事置于同一框架中,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军爱民、民拥军”的革命史诗画卷。在塑造革命英雄形象的过程中,作者既完成了对时代精神的回应,又深度挖掘了彼时风景中所蕴含的侠文化基因,并通过革命话语的规训使其逐渐升华为集体主义的精神图腾。事实上,对“红嫂”本事的考据并非简单的学术求真,其背后是文化接受与意义生产过程中多重力量交织的结果。如何在当下激发和巩固革命信仰对人民群众的感召力?或许从中国现代革命历史题材由“本事”向“故事”转化的文学创作实际出发,对蕴藏其中的民间文化进行重新挖掘和再阐释,是增强“红色经典”自身感召力并使其进一步大众化而得以推广普及的崭新着力点。
二、从私义到公理:侠义伦理的政治美学转化
虽然十七年时期的革命文艺无法摆脱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作家对生活的切身感知及其艺术的真诚,也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全部归结为作家的“应时之作”。事实上,“这种文艺来自中国革命的深处,而研究者未必比当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含50至70年代多数作家)更能深刻地体验到当时的民生,更能睿智地判断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与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如果仅仅是用“政治化’来概括这个时期的文学,用‘集权专制"底下的意识形态的附属品的文学来给予定位,这对那个时期的人是不公平的”?。革命作家的“在场性”经验使其对彼时事件和场景感触深刻的同时,能够更加深入地透视潜存于彼时民间话语中的革命伦理。他们自身强烈的写作愿望以及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都隐含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轨迹的走向,即齐心协力创作有关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因此,作家们自觉地肩负起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通过“人民一战士”的书写再现战火中人民与军队之间的情谊,并力图完成使下一代“知道我们的革命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解放事业是怎样取得的”?之爱国主义教育任务。正是这种书写搭建起了民间道德和革命话语的桥梁,将民间大义升华到革命信仰的高度,为我们重新发现和阐释革命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十七年时期,沂蒙文学“受制于彼时的颂歌式语境,他们对于沂蒙精神的书写因毫无例外地采取纯化策略而终使其深陷于概念化泥淖”。不可置否,作为沂蒙文学主要作品之一的《红嫂》,其创作的确曾受到过时代语境的影响,但其鲜活的故事和生动感人的军民鱼水之情却突破了概念化的局限。文本讲述的“乳汗救伤员”的故事既是对时代政治与大众文化需求的响应,也是作家在强烈写作意愿驱使下的文艺产物,更是将民间叙事转向革命话语、将民间侠义精神与革命信仰融合的范本。小说《红嫂》集中展现的侠义精神并非传统武侠故事中所标榜的江湖义气,而是根植于中国革命历史背景下的一种特殊精神气质和义勇行为。它融合了传统侠文化中舍己救人、扶危济困的民间话语以及现代革命精神中的家国情怀、集体主义革命话语,是侠文化与革命话语在碰撞交融中产生的颇具现代性的精神特质。具体到文本中,这种革命侠义精神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舍生忘死、义无反顾的义举。无论是本事中的红嫂还是故事中的红嫂,她们都在敌人扫荡搜捕的极端危险情境下,冲破一己私利的狭隘观念和封建思想的束缚,大义凛然地用乳汗救助了濒死的革命战士,并将其藏匿于空坟或秫秸垛中躲避追捕。这一行为超越了普通层面的人道主义救助,体现了对民间大义的忠贞坚守和极致践行。即使救助战士的行为直接威胁到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红嫂也是义无反顾地“照顾伤员吃喝、为他洗伤口、敷些简单的草药”③。在还乡团严格的监视和残暴的威逼下,红嫂机智地躲开敌人的眼线,想方设法为战士补充营养,这种行为诠释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侠文化内涵。她以弱者的身躯肩负着扶危救困的使命,完成了对暴力的反抗,显然是一种革命侠义精神的生动写照。
其二,民间道德与革命信仰的融合。红嫂所在的沂蒙山区,深受儒家、墨家等文化的熏陶,儒家的“仁者爱人”“舍生取义”和墨家的“兼爱非攻”“以义为贵”等思想中所蕴含的忧患意识及救世精神早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于沂蒙儿女的文化心理深层。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挺身而出,勇赴国难,他们“用小来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③,慷慨地献出“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这不仅是沂蒙人民侠义爱国壮举的真实写照,更是他们无私奉献、勇于抗争、敢于牺牲的革命侠义精神的现实表达。小说中红嫂救助彭林时,作者这样写道:“开始,红嫂征了一下,当一认出这是一个自己部队的革命战士以后,红嫂感到一阵惊喜。”红嫂将彭林视为自己阵营队友的潜意识,体现了一种自觉的阶级认同。文本中多次提到红嫂的革命觉悟,“部队同志为我们打仗,不怕流血牺牲,我能为流血的同志做点事是应该的,这算不了什么!”这得益于她既“参加过减租减息、反奸诉苦的群众运动,斗争过地主”,又“参加了识字班”,并且战士们经常“给她讲革命的道理”。?正是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红嫂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民间道德逐渐转化为坚定的革命信仰。她将救助战士当作保家卫国的另一种途径,更是在家人与战士之间的艰难抉择中,能够深刻地意识到“干革命工作要有牺牲精神”。于是不顾婴儿的哭喊,将乳汁留给更需要营养的小战士。红嫂这种将个人命运和人民解放紧密相连的精神,契合了革命叙事中的“人民性”想象,其身体由“自然身体”向“革命身体”的演变过程,赋予侠文化更宏大的意义,实现了侠义伦理从私义到公理的价值转变。
其三,快意恩仇和为人民献身的话语蕴藉。小说《红嫂》中除了红嫂“乳汁救伤员”这一曲折动人的情节线索之外,最牵动人心的故事线便是红嫂智斗刁鬼并与其近身搏斗的场景。文本通过对刁鬼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和主体行为的书写,既凸显了红嫂崇高的革命觉悟,又巧妙地植入了红嫂丈夫吴二由胆小落后到思想觉醒的过程,体现了党的革命思想的强大感染力和影响力。面对刁鬼的多次骚扰,虽然红嫂“就像吃到苍蝇一样感到恶心”?,但是仍绞尽脑汁地与其周旋,防止敌人发现伤员的踪迹及对自己“木头疙瘩”般的丈夫下毒手。在转移伤员的当天,红嫂以身为饵,将刁鬼引入家中,“抓过来一把早已准备好的菜刀,刀光一闪向刁鬼头上劈来”,接着“两人就扭在一起”,红嫂“一口咬住敌人的左肩”,吴二用“一个大锕头”砸向刁鬼的脑袋,一起将敌人杀死。③刁鬼的结局,既是红嫂向心怀不轨之人复仇的应有之义,又是她以实际行动带动丈夫思想觉醒而奋起抗争的集中体现,为胆小愚昧的吴二与刁鬼搏斗以报辱妻之仇的行为赋予了为人民除害的价值内涵。故事中的另一主人公彭林排长不但是一位侠文化的践行者,更是革命信仰的坚定拥护者。作为一名战士,彭林尽职尽责、坚守诺言。在掩护部队过河的阻击战中,他以自身性命作护盾,屹然不动地坚守阵地,顽强地“抗击着数倍于我的敌人”?,出色地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这一举动深刻地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的侠者风姿和严守军纪的政治觉悟与革命信仰。即使在负伤养病期间,他也不顾伤痛的折磨,迫不及待地想要返回战场,高喊着“叫我走!我要去战斗!要去为人民立功”?,感慨着“你看!
人民对我的恩情有多么深啊!现在敌人进攻沂蒙山区,人民在遭受苦难,这时候,多么需要我去战斗啊!”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话语,既饱含着侠士知恩图报的意蕴,又氤氩着浓浓的军民鱼水情。纵览全书,小说中众多人物的行为充满了“快意恩仇”和“为人民献身”等话语蕴藉,既是对传统侠文化中“快意恩仇”的民间话语的生动诠释,又通过政治伦理的置换使其升华为“为人民献身”的革命话语,体现了革命信仰对侠文化的现代性改造。
《红嫂》中既书写了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战士,又歌颂了在战场之外辛旁付出、为革命默默贡献的普通民众,使文本深层中充盈着舍己为人、大义凛然、知恩图报的精神气质。从民间话语层面看,是对传统侠义精神的生动再现;从革命话语层面审视,则是对革命信仰和军民鱼水情的生动诠释;从时代层面来讲,它所蕴含的侠义精神突破了传统的框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意味着传统侠文化在革命话语的规训下,侠义伦理发生了政治美学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从民间道德走向革命信仰的可能。
三、跨媒介视域下侠义精神的重构
从理论层面出发,文学经典的跨媒介传播,强调文学经典影视剧改编的文化启蒙和大众普及的传播功能。这种文化启蒙和大众普及的功能,使十七年时期的众多红色经典通过跨媒介传播,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并有力地推动着自身经典化的进程。作为十七年时期流传至今的文学经典《红嫂》,其生产、传播与接受各个环节都充满了跨媒介传播的质素。红嫂精神作为沂蒙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不同体裁和媒介间互文性的跨界传播,使其所蕴含的侠义精神通过对典型事件的符号化处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与升华并深深地扎根于广大人民心中,为大众红色教育贡献了自己独特的力量。
“红嫂”不单单是一个具体的人,它指向的是一类群体,是沂蒙山区广大妇女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展现出的优秀品质和感人事迹淬炼浓缩后的集合体。正如李子超所言:“近来有的人写文章说,沂南县某某大嫂就是‘红嫂’,有的人说沂水县某某大嫂才是‘红嫂’。其实,她们都是在战争年代掩护伤病员有贡献的人物,但她们不是‘红嫂’,而是‘红嫂’式的人物‘红嫂’仅是其中的一个。”?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时期,正是胸怀民族大义的红嫂们的出现,像母亲般地呵护着无数革命战士,为革命的胜利贡献生生不息的力量,才有了我们当下的幸福美满。明德英“乳汁救伤员”、祖秀莲冒死救助郭伍士、张淑贞保护革命英雄的后代,以及无数为战士缝补衣物、传递情报却未留下姓名的红嫂们的侠义行为,再现了平民化的侠义精神,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精神的集中体现。与传统侠士多聚焦于个体英雄不同,《红嫂》中人物的义勇行为经过不断扩散和聚合发展,使得沂蒙地区民间道德中潜藏的侠义精神在革命斗争的历练和洗礼中焕发出巨大的能量,成为沂蒙精神中的重要质素,而红嫂精神也成为沂蒙精神谱系中的重要一环。这种由侠义精神和革命精神相融合而产生的特殊精神气质随着跨媒介的广泛传播,从沂蒙大地的历史褶皱中渐渐走向大江南北的辽阔旷野。
最初,红嫂的义勇事迹以民间故事的形态,通过口头媒介在特定“场域”内进行传播与接受,但受限于传播范围和媒介形态的影响,其革命意识形态未完成国家话语的编码转换。一次偶然的机遇,刘知侠获悉了“乳汁救伤员”的红嫂本事,并被“红嫂”义无反顾、救死扶伤的义举所震撼,促使其以饱满的情感完成了从本事到故事的“陈述形成”的过程,让原本碎片化的侠义事迹获得了系统性重构。1961年,小说《红嫂》的诞生,标志着故事叙事媒介的范式转移,为红嫂“乳汁救伤员”的义勇事迹由民间道德置换为政治伦理提供了有力的文本支撑,推动了革命话语和侠义精神在文本层面的意识形态缝合,形塑并推动了侠义精神内涵的现代性转化。而纸质媒介的介入,拓展了红嫂事迹的传播广度,使小说《红嫂》迅速以自身所具有的魅力衍生出一批跨媒介艺术作品,再次实现了叙事模式的转变,兴起了一阵“红嫂热”。1964年,同名小说被改编为现代革命京剧《红嫂》。“红嫂”这一女性英雄形象经由京剧演员“玲珑剔透”的演绎,以更加直观的戏剧动作和声情并茂的演唱再现了红嫂大义凛然的义举,使其从平面的书本中直立起来且更加饱满;加之毛主席对其“充分体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的点评,更是推动了红嫂本事和红嫂精神在名角效应与政治话语的影响下,由审美场域向政治场域渗透。值得注意的是,在1964年全国文盲率 38.1% ,甚至饰演“红嫂”一角的张春秋“识字不多”的社会语境下,戏曲《红嫂》凭借其视听结合的综合优势,成功突破了文字媒介的传播壁垒,实现了革命话语的下沉传播,这是小说《红嫂》所未能企及的。由此来看,京剧所具备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对底层民众的影响不容小。它作为小传统更为大众喜闻乐见,其说说唱唱形式的京剧更能走入群众中去,是大传统在民间传播的重要媒介和载体。此后,接踵而至的芭蕾舞剧《沂蒙颂》和1997年上映的电影《红云岗》以影像化媒介为“红嫂”侠义精神的传播和转译,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不停地转动着红嫂精神历久弥新的齿轮,实现了革命历史记忆的当代活化。无论是小说中的叙述话语,还是芭蕾舞剧中的肢体动作,抑或影视剧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它们都为重构“乳汁”这一符号系统和强化红嫂精神中的民间大义和革命话语而努力,更为当下如何增强“红色经典”的自身感召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跨媒介传播的热烈反响,为小说《红嫂》的经典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从深厚的革命土壤里挖掘、提炼的“红嫂”形象经由不同媒介的演绎,显得愈加丰满,使红嫂身上那种义无反顾、大义凛然、坚韧顽强的侠义精神在革命话语的规训下转化成为人民献身、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信仰,推动了“红嫂精神”的家喻户晓和与时俱进,使“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的嘹亮歌声持续回响在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为纪念红嫂们的侠义壮举及保留沂蒙地区独特的文化记忆,沂蒙地区成立了“沂蒙红嫂纪念馆”,以文字、声音、图像、影像等多种手段,向广大群众转述红嫂们的侠义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当下,先辈们义无反顾、临危不惧的革命侠义精神被转化为迎难而上、勇于开拓、砥砺前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激励着今日的红嫂们继续沿着先辈们所开创的道路,为沂蒙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沂蒙精神的弘扬贡献自己的力量。
《红嫂》的跨媒介传播实践不仅实现了红色经典的意义再生产,而且揭示出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物质载体的潜能。其所蕴含的革命话语和民间伦理相交融的艺术特质,通过小说到戏剧再到影视的跨媒介传播,既推动了自身经典化的进程,又为红色经典激活自身生命力提供了一种范式,也使明德英、祖秀莲、张淑贞、梁怀玉等红嫂们的侠情义举由沂蒙山区走向了全国各地,使“红嫂”形象逐渐演变为大众文化中的革命侠义图腾,为人民群众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和价值引领,实现了教化与民间审美传统的有机融合。
结语
在《红嫂》由“本事”到“故事”的演变过程中,作者抓住红嫂“乳汁救伤员”的肉体献祭,将传统侠文化“轻生死、重然诺”的个人英雄主义转化为“舍己为公”的现代革命主义精神,不仅完成了对革命精神的文学建构,而且推动了革命话语对传统侠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这种改造和转化并非简单的政治祛魅,而是通过叙事话语的价值转变及跨媒介的多重演绎,将“红嫂”塑造为兼具母性光辉和革命英雄特质的崇高符号,使其成为沂蒙精神乃至中国革命红色基因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对民间侠文化的再生产,既暴露了革命叙事的世俗化困境,也印证了侠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它始终在历史资源和现实文化的张力中寻找新的栖息地,持续不断地释放自身的价值光辉,这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文化逻辑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
注释:
① 李子超:《李子超诗词选》,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349页。② 袁成亮:《革命现代京剧〈红嫂〉诞生记》,《党史博采(纪实版)》2007年第2期。③ 刘开宇:《崇高的思想,感人的形象—京剧〈红嫂〉观后》,《戏剧报》1964年第8期。④ 孙士生:《小说〈红嫂〉及其跨媒介传播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⑤ 参见杜守恒:《“红嫂”原型明德英》,《山西老年》1994 年第8期;关捷:《平凡的圣母—访红嫂原型明德英》,《党史纵横》1995年第6期;张建国、李振兴:《“红嫂”明德英》,《春秋》1998 年第4期;贺俊杰:《红嫂和〈红嫂〉的故事》,《世纪》2006年第3期。⑥ 参见宋桂花:《从劳动解放到妇女解放:新文化史视角下红嫂劳动叙述研究》,《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宋桂花、杨克:《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红嫂”形象的重构研究》,《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张元珂:《绽放在沂蒙大地上的民族之花——沂蒙精神与沂蒙文学互源互构发展史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⑦ 徐玉如:《文学地理视野下的沂蒙文学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⑧ 陈夫龙:《边缘的激情: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62页。⑨ 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① 张均:《转换与运用:本事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①④⑤①②③④⑤③⑦③②③刘知侠:《红嫂》,《一次战地采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15页,第117页、第120页、第120页、第121页,第121页,第119页,第115页,第98页,第110页,第121页,第125页,第148页、第148页、第148页、第149页,第103页,第91页,第93页。
① 临沂地区史志办公室编:《临沂百年大事记》,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5页。
① 张建国、李振兴:《“红嫂”明德英》,《春秋》1998年第4期。
① 张均:《重新打开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文艺》,《文艺研究》2024年第7期。
① 陈晓明:《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
① 知侠:《充满战火气氛的创作道路》,《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
① 张元珂:《绽放在沂蒙大地上的民族之花一—沂蒙精神与沂蒙文学互源互构发展史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② 岳光东:《“小推车”精神不能丢》,《人民日报》2014年5月20日。
③ 刘叶琳:《文学经典跨媒介传播的观念演变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页。
③ 李子超:《李子超诗词选》,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349页。
③ 滕久昕:《看〈红嫂〉有幸见到毛主席》,《先锋队》2013年第34期。
③ 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1982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12周岁以上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人)为235,820,002人。同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数字比较,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38.1% 下降为 23.5% 。
③ 陈巨慧、张旗:《从《红嫂〉到《红云岗〉》,《大众日报》2010年5月12日。
③ 翁思再主编:《绪论》,《京剧丛谈百年录(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文学侠义书写与中国形象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3BZW129)的阶段性成果。枣庄英才集聚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当代山东抗战小说的侠义书写与山东形象研究”(2022年度)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