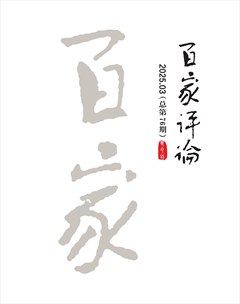内容提要:潍坊的文学传统对当地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深远持久的,这种影响既体现在地域文化的传承中,也渗透进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文学不是高阁上的摆设,而是化作了“萝卜雕花”般的世俗智慧——既有粗的生命力,又不乏精细的审美。在快节奏的当下,潍坊的文学气质如潍河暗流,持续滋养着这片土地。它教会人们用故事的眼光看待平凡,用飞翔的姿态面对生活——正如那些翱翔在渤海风中的风筝,根系扎在泥土,翅膀却永远向往苍穹。这种“扎根”与“超越”的平衡,或许正是文学赋予这座城市最珍贵的礼物。
达索·萨尔迪瓦在《“大部头”的秘史: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何写出〈百年孤独>》这样写道:“显然,墨西哥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两座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大城市,成就了《百年孤独》的写作和出版。”
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是由他所在城市的山水人文养育而成的,这座城市是他艺术的原乡。这座城市的气质,也是作家的气质。我经常想,潍坊——这座坐落于山东半岛中部的城市,它是何种文学气质?它是怎样引领这座城里热爱文学的人们,一步步走出去的?每当此时,我的脑海里会慢慢拉开一幅浸染着千年墨香与烟火气息的卷轴,它里面既承载着齐鲁大地的文化厚重,又流淌着民间生命的鲜活诗意。
潍坊古称“潍县”,郑板桥任潍县知县时“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诗句,将文人风骨与市井悲欢糅合,奠定了这座城市文学精神的底色。峻美的东镇沂山,三山叠嶂的驼山、云门山、玲珑山,浩浩汤汤的潍河、弥河、虞河,清代珍藏过万件玺印和吉金重器的万印楼、“鲁中明珠”江北第一私家园林十笏园这些丰厚的创作资源深深影响和引领了我,让我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文学之路。
小时候过年,我最大的爱好是去别人家串门。因为那时每家每户要在屋里贴年画。这些表面看似静止刻板,实则古老神秘的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令我深深着迷。
不管去到谁家,我都会迅速脱掉鞋子,站在他们家的炕上,一幅幅认真地看炕头画、窗画、卷轴《嫦娥奔月》《孔融让梨》《梁祝化蝶》《蟠桃大会》这些年画里特有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令我大开眼界。我不知道姜太公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本事,能让海水后退,退出个寿光清水泊和滨海;我也不知道曾任北海郡(即后来的潍坊)太守的孔融,是否真的能在一盏茶的工夫,请到刘关张解北海郡之围。我只知道,在没有人的角落,我会模仿姜太公的样子,用手指着前方,也想退出一个五彩斑斓我独自拥有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我想象力的呈现:海水会说话,蟠桃能从天而降,嫦娥舞动衣袖,萤火虫即刻变成洁白的月光,而孔融真的能腾云驾雾,在刀光剑影间飞奔……
杨家埠年画用一纸距离,让故事走近现实,让一个孩童单调的童年充斥着五彩缤纷的光影。它为我拓展出了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的真善美和惩恶扬善,是我三观初始的建立。长大后,我经常想起这些。潍坊的文学气质既有郑板桥这种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又有潍坊年画中乡野的诙谐与生命力,它丰厚的文化底蕴,才有了我以后在文学道路上的坚守和勤奋。
那时,放学后,我喜欢跑去妈妈单位对面的书店等她下班。因为个子矮,每次我不得不费力趴上柜台,聚精会神地挑选里面架子上的书,然后恳请书店的阿姨拿给我读一下。捧着那些书,蹲在柜台的角落里读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还书的时候,书店的阿姨还特意问我两句,里面写了什么呀,你看成这样?我兴奋地给她们讲书中的故事,讲的时候,我添加进去自己对故事新的想象。这些书,让我认识了人性血脉,认识了山川万物,让我对外面的大千世界,有了新的辨识和想象。
四年级的暑假,我在一家租书屋里,第一次见到了《红楼梦》。站在书架前,我被书中林黛玉的“偷得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惊得呼吸不畅。我问自己,世界上怎么可以有这么美的诗句出现?读着它们,让我感觉自惭形秽和室息,我永远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红楼梦》像是一扇通往文学世界的窗,推开它,我看到了外面浩渺如烟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