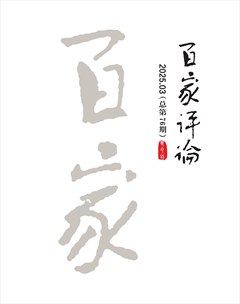内容提要:乡村作为文学想象中的地标,历来对乡村的书写中呈现出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格局。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乡村处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乡村叙事的文化逻辑发生转化。安亦然的《听,星星的耳朵在唱歌》突破了既有的城乡二元对立叙事,展现出新乡村在文化语境变化下多元共生的局面。文本通过星星一家的家园重建,折射新时代乡村大家园的振兴。新乡村建设下,乡村个体不再是被动的拯救者,并在深层次上体现出家园重建是一次现代人们回归自然的精神还乡。文本站在乡村变革的历史语境下,探讨现代性童年这一课题,指出现代性的分裂不可避免,但乡村与城市对抗的经验会在儿童的生命空间中彼此融合。
乡村在文学中“始终作为不可忽略的参照坐标坚硬地存在”①,现代社会的历次变革都会与乡村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相互交锋。在历来的乡村叙事中,都“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叙事支点,那就是从文化选择、价值判断到思维模式,艺术结构贯穿的二元对立”②。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使乡村在与城市的对比中,始终是处于落后、封闭的他者地位。在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乡村再次处在新的社会变革之中,乡村叙事的历史文化语境也开始转变。对于乡村和乡村儿童的书写一直是儿童文学的传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儿童文学书写了一大批关于乡村儿童的文学作品,它们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儿童的生存现状与精神成长的困境。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儿童文学通过童年叙事参与到乡村书写中,并以自己特有的美学特征展现新的童年景观。《听,星星的耳朵在唱歌》就是这众多作品中的一部。这部作品展现了在新时代振兴乡村的策略下,儿童成为新乡村的见证者与受益者。文本借助儿童视角,以乡村的角度回望城市,突破了传统的城乡割裂的二元叙事格局。作品巧妙地将儿童个体家的建设与时代政策下的乡村建设合二为一,以个体的“家”折射乡村的“大家”,以“我”喻“我们”,在叙述中展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多重童年景观。
一、突破城乡叙事对立
儿童文学中一直存在着对乡土、乡村童年的书写。这类书写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成人作家回望自己的童年经历,将自己的目光投向童年乡村生活经验,展示出故乡的风土人情。这类作品中乡村作为童年发生的物质载体,容易在记忆的美化下,使乡村童年呈现出田园牧歌的氛围。另一类则是站在乡村儿童贫困的现实问题上,关注乡村儿童成长面临的困境,儿童在成长中的缺憾与痛苦。而这些作品容易将城市作为拯救之地,城市成为“拯救乡村的捷径,被反复勾勒成美好的希望所在”③。这两类创作倾向的作品在对乡村生活的描写,始终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城市“是现代生活世界的空间场所”,是现代性的物质表征。乡村则是城市生活对照的地点,这个地点被赋予了超出乡村本身的意义,转化为现代性下的审美对应物,与城市相比乡村是另一层审美上的生活场域。
因此不可避免对乡村产生了两种审美态度,一种基于现代性是“不断地进步”,城市生活是发达、进步的表征,与此相对应的乡村则是代表着落后、顽固。因此对乡村儿童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揭露,总容易意指一种光明的城市生活。但“现代性的每一个层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遭到了反诘和批判”④,在对现代生活的赞扬和乐观的情调中,一种对于过去田园生活消逝的忧愁也始终伴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另一重审美中,乡村就成了乡愁的代表,“乡村生活被看作是象征理想社会秩序的田园诗”。在现代化的关照下“乡村”成了遥远的逝去。
不论是对消失的田园生活的追忆,还是对乡村落后性的批判审视,这些都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即现代性上审视着乡村,将乡村作为城市的“他者”。在乡村这面他者之镜中,映出了城市的先进、发达、繁荣、冷漠、麻木等特征。这也是城乡叙事中固有的叙事特征,以城看乡,即以城市为主体看待处于地缘边缘的乡村,其最终指涉的仍是城市这一主体。在这种叙述方式下,乡村始终是城市的对立面。而在《听,星星的耳朵在唱歌》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儿童视角看待乡村,借助星星的生活旅程,改写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割裂叙事。
地理景观是人们在与自己的文化互动中通过实践活动而产生的物质形态。地理景观在形成的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③对此,“地理景观是一个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而社会就是建构在这个价值观念之上的。”③乡村生活中,星星跟着爷爷一起去放牛、捉蛔蛔,遇到下雨,便顶着荷叶回家。在院子里同小花狗玩耍,看春天梧桐树开花,夏天听蝉鸣虫响,等秋天石榴开嘴笑、梧桐落叶。星星生活的乡村生活一年四季都充满了乐趣。乡村地理景观将个体纳入自然的轮回之中,个体生活的场所虽然以建筑物的形式与自然隔开,但是个体所生活的空间仍位于乡村自然之中。这体现出乡村地理景观的一体性,“乡村生活总是要将人纳入整体中”③,生活在乡村中的人被纳入自然环境之中。星星在与乡村自然的接触中生成了自己的观念,小花狗是可以和自己交流的,蛔蛔是歌唱者。乡村养育了星星的灵动与自然。
城市则是另一种生活景观。星星从车站回出租屋的时候,他们坐的摩托车无法爬上城市高架桥。星星赞叹着“街道干净而又整洁,这就是大城市啊”“路两边的法桐长得整齐而又漂亮,这些树和农村的树不一样”。在城市的规划中,人们将自然景观纳人,有序、整齐的自然植物与野生自然形成鲜明的反差,“在那里自然被调遣、被驯服甚至被折磨”。城市空间上的划分,体现人对于自然的掌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
城市的地理景观与乡村的地理景观截然相反,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和价值观念。而“儿童拥有一个独特的精神天地,有着他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对各种人事的价值评价标准。”①在星星的视角中,城市中的小狗都是规规矩矩的,“不对人乱叫,也不闹,乖乖的样子”①,自己的小花狗是“总是爱闹,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的”?。城乡之间的不同在儿童的视角中展开,尽管这里的小狗狗们穿着的衣服比自己身上的裙子还要干净漂亮,脖子上戴的铃铛也比小花狗的精致。但在星星的视角里,一只小狗被拴起来,没有了自由会发狂,“狗嘛就应该有狗的样子,城里的这些狗嘛,相较起来还是小花更可爱”。在儿童视角中,城市所体现出的地理人文景观,正是一种异化,这里的动物、植物都是被规训、被束缚的。城市作为乡村的他者折射出其异化的面容。
小说以儿童自己的视角质疑城乡之间的等级,而实现人与万物平等相处的观念,质疑二元对立观念。新乡村建完之后,星星的妈妈说“农村不比城市差了”,陈菊从城市来到新乡村感叹:新农村像富人的别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