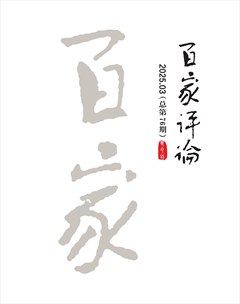内容提要:《散文课》是一部研究散文本体的学术著作。作者以叙述者为突破口,揭示叙述者的形态决定散文文体的形态,从而梳理出散文的本质与动力。他采用纵横交错式的研究思路,在中西理论研究的交点上,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开拓了散文研究的新疆域。
关键词:叙事学叙述者动力元辨体方法
散文,是最基本的文体,也是与人们生活最近的文体。在日常生活中,散文的出场频率远大于小说和诗歌,后两者的生产与传播都需要特定契机,而散文几乎是每个人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接触并训练的文体。另一方面,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却容易使人忽略关于散文的本体问题。既然散文人人可写,又如何鉴别其优劣?当代散文和以往散文相比,又有哪些异同?在今天,要想把散文写好,又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王彬的《散文课》系统地回答了以上问题。这既是一本关于散文的教学著作,又是一部指向散文本体研究的学术著作。丰富的资料信息、扎实的学理基底、自信清晰的论证,都增强了本书的辨识度,使其明显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散文教材 (或作文教材),在当代散文研究中独具一格。王彬的思路,并非“为授课而授课”,更不是“为评论而评论”,而是带着问题上路,将困惑当代散文的诸多问题一一抛出,条分缕析,逐一解答。在研究过程中,作者运用叙事学、文本细读等来自西方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古代文论,从辨体、叙事、法度、修辞、创作五个方面对散文进行解构与梳理,从而开启了散文研究的新大门,展示出一个五彩纷呈的散文世界。
其中,辨体和叙事是本书核心问题。传统的散文研究,常常把法度、修辞、创作等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强调散文的审美属性。本书则在叙事学的视野下展开,用相关方法探讨文体本身,分析散文中未被他人重视的叙事构成,从根子上,强调散文的文体属性。此即第一讲《辨体》与第二讲《叙事》之要理。据此为基础,再结合对法度、修辞、创作的研究,从根苗到枝叶,由内及表层,多方位地论述散文的特点。因此,辨体和叙事如同全书总揆,书中诸议题皆围绕二者展开。本文亦以这两大问题为主,分析王彬的散文主张,抓取出散文文体的“常量”,进而窥视当代散文的面貌及进程,总结出散文研究的新思路。
顶多只是批评它不够好,而不是质问“这也是散文吗”。要知道,“这也是诗吗”“这也是小说吗”的质问,一直伴随着转型后的诗歌和小说。这或从一个侧面说明:散文中隐藏着某些不变的、极具说服力的“编码”,它们决定了散文的文体边界;无论散文的形式怎样变化,都是在这条看不见的边界线内做文章。故而读者对于散文的文体界定,大致是心中有数的;哪怕不能准确地说出个中缘由,也能靠直觉推定某个文本是否属于散文。
但这并不是说散文简单。正因散文的边界比诗歌、小说等更固定一些,对散文的判断也就更具模糊性一毕竟在固定的边界内,相似文本的繁衍能量是惊人的;既然不相上下,又何论孰优孰劣呢?如今,很多人都能写出文从字顺的散文,这更增加了散文的鉴赏、判别难度。针对这一现象,王彬在《散文课》的序言里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散文是一种复杂的文体”°。因为复杂,所以更需要辨析,需要明确这一文体的内涵、特点、边界、外延等一系列问题。
辨体,是写作的开始。王彬对散文的辨体从三个维度展开:
一、辨体:何为散文
现代化的进程带动了诸多事物的转变,文学亦然。不同文体都在这一进程中革新,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带动了中国文学的转型:“从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今天,中国文学完成了现代性对汉语写作各文类的初步探索。”①与诗歌、小说等文体相比,散文的转型虽也有过短暂的热潮,但似乎没有引起太大争议。新诗因为走在各种文体实验的前端,发展速度远超于大众平均接受范围,故常被质疑、诟病。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也挑战了人们既有的阅读经验,被普遍认为“读不懂”。而散文,也从文学革命的文白之争走到今天,关于散文文体的合法性,却一直以来少有非议。如果一篇散文质量欠佳,那么人们
一是对比。王彬区分了散文的实用性与文学性。因为散文既可以偏实用,又可以偏文学,故很难界定。王彬的看法是,散文的根在于生活性(实用性),“进入文学范畴的散文少之又少散文必须符合文学规律。‘实用’与‘文学’是散文的两端”③。在《散文课》里,王彬讨论的对象主要是文学性的散文,而不是实用性的散文,如应用文。
二是文学史的梳理。《散文课》从史出发,详细地介绍了散文的流变。在中国古代,散文在不同时期被称为辞赋、骈文、古文、小品等。现代以来,西方的essay影响了中国散文的样式。围绕着这一现代性之变,还有美文、随笔、絮语等概念产生。在时间的筛沥下,有一些命名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在约定俗成的范畴下,篇幅较长的被称为散文,篇幅短的是小品,突出文化含量的则是随笔。今天,人们说的散文就是这三者的统称。
三是从叙事学角度来辨析。《散文课》最新颖也最精彩的是以叙事学(narratology)为“地基”,结合中国传统的叙事理论,创造性地阐释了作者对当下散文现象的梳理与认知,从而使本书明显区别于其他的散文研究专著。叙事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就曾指出叙事普遍存在:“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④但直到20世纪中后期,在结构主义的大背景下,叙事学才开始产生并勃兴。散文本身是一种叙事性突出的文体,若从叙事学的方法切入,有很多问题都值得一探究竟。遗憾的是,用这一方法来对中国现当代散文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目前还并不多。
以叙事学为窥视镜,王彬抓住了散文文体的核心特征。其中有两点尤为关键:第一,第一人称;第二,叙事围绕个人展开。第一点,使散文有别于小说。小说中的人称视角是多样化的,除了第一人称,常见的还有第三人称,偶尔也有第二人称。但小说里的第一人称“我”,一般并不是作者本人,哪怕表面写“我”,内里也是写他者,因此小说是一种“他叙事”。例如,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用的就是第一人称,但书中的“我”并非夏洛蒂本人。而在散文中,文本叙述者“我”,则对应作者本人,叙述者与作者是合一的,是一种“我叙事”③。所以读者在读到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时,自然知道作者写的是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