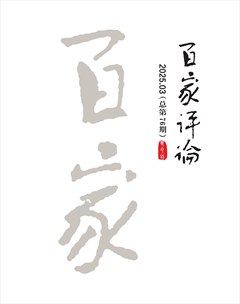内容提要:“学者型作家”房伟新近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杭州鲁迅先生》敏感地捕捉到历史裂隙处所发出的喃喃低语,理性审视当代现实生存处境,并辐射科技时代浪潮下暗涌的未来寓言。其对历史的大胆重构与狂想实验拓展了小说的叙事边界,也为我们探索历史、反思当代、预见未来提供了新的视角。作者在小说中以元小说的连环套层结构形塑多重时空,实现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微妙互通,又将视线投向边缘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世界,探寻历史与现实表象之下的生命本质。聚焦于“作家与死亡”这一命题,作者寻绎着死亡对于人类的精神意义,书中大量关于死亡与疾病的隐喻,賡续和转化了五四启蒙文学传统,既书写了边缘知识分子卑微苦闷的生存困境,又传递出作者反思人类未来发展的现代性焦虑。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重“史"传统。文学的“补史”功能,一直以来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文学叙事。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记忆围绕着民族存亡与战争体验而展开,形成了几蕃革命历史叙事的浪潮,并在十七年时期成为主流。然而此前的历史文学叙事,“主要还是受彼时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而将丰富复杂的历史生活过分政治化、简单化。”①即使是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写作,也不过是“将历史化为新的消费传奇”②,而无能提供文学如何书写历史的新模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房伟的系列历史小说做出了有益的文学探索。《在历史的灿烂星空之下》一文中,作者认为“真正现代的历史小说,应该是想象力的虚构与对历史真实的寻找共存的精神诉求。文学既不是仰视历史,将之视为最高准则,也无需俯视,以肆意的怪诞夸张,以虚无的虚构,践踏历史真实的存在。在历史小说之中,文学和历史,应该是一种‘平视’‘交流"的关系。”③在其中短篇小说集《杭州鲁迅先生》中,为达成这种文学和历史之间的“交往合理性”,作者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并置,以诗学的方式赋予“历史材料”以血肉和灵魂,用故事的叙述为历史多维面向的“复原”提供了可能性,使历史亦犹如“一粒在金字塔内无气无息秘密掩埋的谷物种子,历经了数千年的封存,仍能够保持生根发芽的潜力。”④在作品中,房伟凭借学者身份自由出入于文学史料与文学典籍之中,以元小说的连环套层结构形塑多重时空,构设互文语境,实现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呼应与对话,并将视线投向边缘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世界,探寻历史与现实表象之下的生命本质。作者还通过几种不同的死亡方式想象作家死亡前的种种,还原其间具体的时间刻度,用死亡抵抗现实压抑,重新想象和讲述“人类精神至暗时刻的喃喃低语”。在赋予人生庄严感的同时建构起了自身文学的合法性,也展现出作家将时代、历史和个体生命问题置于小说深层结构的多重尝试。小说集所收录的八篇作品中,“有的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底子”,打捞起历史进程中那些被忽视或遮蔽的面向,并在历史理性基础上描摹历史中的人的心灵际遇和生命体验。而有的则是“充满隐喻的未来狂想”°,以谱写科技时代文学何去何从与人类情感无处依附的未来寓言,传递出作者反思人类未来发展的现代性焦虑。
一、狂想的可能:多重时空与精妙叙事
历史记录已经发生的事,它的书写往往代表着官方的、权威的、被认可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而文学折腾可能发生的事,为历史中那些属于个体的、非正统的、被边缘化的诸多可能性发声。本着“任何发生过的事都不应被当作历史的弃物”这一原则,房伟用真实的历史事件筑基,却以文学的方式想象事件背后那些丰富却被忽视的隐秘细节,并以此搭建起一个亦真亦幻的文本空间。小说集里,《“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以《鲁迅全集·三闲集·在上海的鲁迅启示》一文中有关“真假鲁迅”的历史本事展开想象;《苏门答腊的夏天》取材郁达夫的苏门答腊岛流亡经历;《一九九七年“海妖”事件》取材王小波心脏病突发病逝经历;《寒武纪来信》取材张资平的地质学教育背景及其作品;《谋杀女作家》则取材女作家戴厚英谋杀案的侦破始末。这些在文学史中毫不引人注目的细枝末节,在房伟那里,却蕴含着异常强烈的文学吸引力和极其广阔的文学想象空间,成为了其开启狂想之门的密钥。
将这样的狂想落实在小说形式上,《“杭州鲁迅”先生二三事》可作为一则典型。小说采用了元小说的连环套层结构,在文本层面上形塑了历史与现实的二重时空,在“我”与朋友章谦的往来中,又置入了章谦所创作的一则完整的历史短篇小说,构成彼此指涉的戏中戏,借以实现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微妙互通。如果借助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有关叙事层的相关理论,“我”与章谦的交往形成故事的外叙事层,文本中所呈现的章谦的小说原文是内叙事层,在这一内叙事层中,“假鲁迅”又以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展开叙述,构成更深一层的叙述,形成元叙事层。从该篇小说的创作初衷上来看,房伟曾表示:“我读史料的时候,发现杭州有人冒充鲁迅,觉得很有趣。鲁迅也专门写了文章来揭露这个事。这种冒充名人的情况,在当代也有不少。但那个时代的底层小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他与时代是怎样的关系?他们和鲁迅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那种底层生存的知识分子状态,又与当下有着哪些双生性的复杂关联?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只能将一个小人物以丑陋的方式钉在《鲁迅全集》之中,而我想打捞他,让假鲁迅和真鲁迅同处于一个历史关注时空。”③可见作者更为关注的是这个元叙事层中所展开的内容:“我”因被误认为是文豪鲁迅而引起身边众人哗然,于是干脆将计就计扮演起了鲁迅,然而终被戳穿,继而丢失工作的“我”在上海得以窥见真正的鲁迅,在同一时空中“我”守望着“真鲁迅”却永远无法走近他,最后在“真鲁迅”死亡的治丧会场上重操扮演鲁迅的旧业。小说从一个“不过挣扎着‘不死’罢了”的历史边缘知识分子的内心体验出发,观察大时代中普通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历史景象,以及“处于时代”之中的鲁迅晚年寓居上海的情形与“鲁迅之死”所呈现的人间世相。这一独特视角展现了历史的晦暗复杂和历史想象的广袤神奇,探讨了人性、命运和社会等诸多问题。而这些最终又被章谦的一份小说手稿一网打尽。在叙事的最外层,作者同样在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限知视角下勾画了青年教师章谦走向死亡之前的人生片段。在以当代时空为背景的故事中,章谦是作者故事的主角,而在历史时空背景下,“假鲁迅”周预才则是章谦故事的主角,在元小说的嵌套结构中形成历史时空和现实时空的对望,处在不同时空的主角由此展开对话。似乎除了打捞起曾被历史宏大叙事污名化甚至漠视的鲁迅的“假冒的影子”外,还投射了所谓历史与现实的“双维互动”关系。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章谦和周预才具有了同构意义,他们同是历史的边缘人,章谦是世俗意义上“不务正业”的边缘教师,怀才不遇、投稿被退,最终走向自杀;周预才的生存处境“不过挣扎着‘不死’罢了”,他的世俗价值只能依赖扮演鲁迅而获得,所以假冒鲁迅时又时常为自己单薄的生命和卑微的生存感到无比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