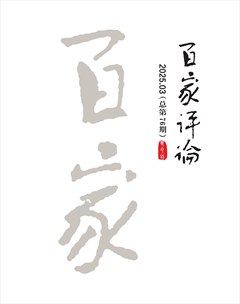内容提要:在青年作家魏思孝笔下,村庄的根脉不再是土地,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村民。从空间上看,失去缚地性与自足性不再是村庄走向解体或已经解体的表现,村庄反倒像是长出了细密的根须,沿着村民出走的足迹与亲缘谱系向乡镇、城市甚至更遥远的地方蔓延;从时间上看,村庄失去了历史的惯性,不再宿命般向着特定的未来进发,它似乎彷徨于无地,但也因凝滞获得了抵御崩毁的力量。面对村庄与历史的脱轨、乡土叙事整体性的破碎,魏思孝征用了源自乡间的话语系统,以冷静与热忱并峙、真实与虚构难分的“听闻叙事”,在村庄“褶曲”的时空中开掘出书写其“当代性”的多种可能。
无论是以启蒙视角对乡土进行批判,还是在“新社会/旧社会”“新中国/旧中国”的对立架构中展现乡村的政治图景,抑或是以乡土的退变呈现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在对现代的反思中发掘乡土的“前现代的现代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似乎始终是一种未完成的社会形态,总是处于“传统/现代”“落后/先进”“农业/工业”“农村/城市”等对立结构的夹缝中,不是通过变革获得新生,就是面临终结的危机。
据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中统计,“从1985年到2001年,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年减少了
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诛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的文明的奠基以及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①。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起,描写村庄的解体、乡土文化的衰微以及城乡之间的冲突成为了乡土写作的重要命题,像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作品,无不聚焦于此。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持续关注乡土文学发展的丁帆还能结合当时的创作实际,对所谓“乡土文学消失论”进行有力地回击:“我以为乡土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的潮头中是呈上升趋势的,面对滚滚而来的社会变革大潮,乡土文学的表现领域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广阔无垠了。”°而到了新世纪伊始,李敬泽在《<上塘书〉的绝对理由》中却不无沉重地写到,“乡土已经处于城市的绝对宰制之下,它已经失去了经济上、伦理上和美学上的自足…乡土在中国现代以来小说传统中的中心位置也已终结”③。
巧合的是,李敬泽提出“乡土在小说传统中中心位置的终结”与李培林出版《村落的终结》都是在距今已二十一年的2004年。而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本文想要追问的,并不是村庄或者乡土文学的“终结”是否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真正完成。近些年来,尤其是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提出前后,《白洋淀上》《雪山大地》《莫道君行早》《宝水》等作品都生动地反映出村庄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韧性与生命力。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似乎很难得出村庄已经终结或即将终结的结论。可不管是建设新农村的美好愿景还是村庄终结的悲观判断,村庄似乎永远蒙受着源自未来的巨大阴影,在线性的时间发展观念中,村庄能否抵达未来,如何抵达未来,又会抵达什么样的未来,始终是乡土写作绕不开去的话题。乡土写作所描摹的村庄的当下,总是预见着未来的当下,其所描摹的历史,也总是为迈向未来提供惯性的历史,这一历史愈厚重,它能预见的未来就愈加明晰。
为了让乡土写作呈现出历史的深度,作家需要以间离之法、远眺之姿,将村庄视作一个整体,放到历史的坐标轴上,完成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洞察和预见。换言之,乡土写作越是厚重,越具有历史感,村庄的当下就越容易被约略为一个坐标轴上的时段或时点。与之相较,从乡土内部发起的观测,往往是“当局者迷”,观测者并不关心村庄从哪里来,也无法回答村庄将去往何处的问题,甚至无法对村庄的概念和边界做出明确的界定,更无法判断村庄所处的历史阶段。但辩证地看,当局者的惶惑避免了过于本质化的乡土想象,周遭现实的嘈杂之声让其无暇对历史和未来展开叩问,而是更执着于对当下的体认与陈述。在短暂而节制的观测中,村庄似乎失去了历史和未来,但同时也获得了时间上的凝滞,它不再是历史的中间物,不再走向命定的终结或复兴,反而在一种恒久的彷徨中开拓着自身的边界,展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乡村图景,而这正是青年作家魏思孝在其乡土写作中惯常采用的观测方法。
一、村庄的隐身与溢散
2024年4月,魏思孝的新作《土广寸木》出版。“土广寸木”,“是对‘村庄’两个字进行的拆卸”—这是作者魏思孝对小说书名的解释。他认为,这一拆字法,正表达了小说的主题,即“从不同的视角,对村庄进行解剖”。对于首次看到书名的读者来说,如没有看到这句解释,“土广寸木”算是一个拗口但并不晦涩的字谜。“村”“庄”二字以及“村”字的左右结构均被颠倒,“土”字也挣脱了“广”的半包围,甚至于在小说的封面上,“庄”还被进一步拆分为“十”“一”和“广”。零散的部首和笔画错落分布,造成了辨识与理解的困难。只有获悉或破译了谜底,后知后觉的读者才会发现,这些看似并无关联甚至有些陌生的字符,原来正是“村庄”二字的拆解。
比起以拆字隐喻对村庄的解剖,本文更加关注的是以“土广寸木”拼凑“村庄”二字时遭遇的梗阻,这一梗阻标志着小说与传统乡土写作产生的疏离一—即便作者以散点透视的方法详尽地描摹村庄的细部,但这些细部组织起来却很难拼凑出那个已经形成共识的、整体性的“村庄”的符码。
与魏思孝的“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近似,《土广寸木》的上篇同样少有泥土的气息,取而代之的是尾气,是粉尘,是浓重的机油味,是寒风里混杂的铁锈的腥味。这些气味来自于叙事的后景,来自厂房、城区、饭店、工地、车间、洗浴中心、劳务市场、废品站、高速公路…这些凌驾于土地之上的现代的空间与造物,同样是村庄的一部分,同样是“村庄”的笔画和部首。
莫言曾说:“一个作家必须创造出一块属于自己的乡土、文学的乡土。”而魏思孝在以自己生活的刘辛村为原型开垦自己的文学乡土时,他所面对的是农村土地被大范围征用,农民“由传统意义上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演变为‘一切农业户口者'”?的社会实际。大量农民从四时有序的农业活动中解脱,但其总体收入情况却没有获得太大改善,即便成为企业工人,在经济下行时,他们也无法获得稳定且高额的收入。与此同时,村庄因为耕地的减少失去了原本的自足性,促使本就不再为土地束缚的农民进一步扩大其日常的活动半径,让走出村庄不再是少数带头人的冒险,而是多数农民维持生计的必然选择。
正如赵坤在序言中所说,“魏思孝《土广寸木》的悲悯之处,在于将历史的主体确定为人”。在魏思孝笔下,村庄的根脉不再是土地,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村民。失去缚地性与自足性也不再是村庄走向解体或已经解体的表现,村庄反倒像是长出了细密的根须,沿着村民出走的足迹与亲缘谱系逐渐向乡镇、城市甚至更遥远的地方蔓延。
最为典型的例子要属“乡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王能好》。得益于交通工具的便利,王能好去了上海打工,他觉得上海的城市生活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也缺乏参与感。而他之所以离开村庄,“不是外面多吸引人,而是眼下的生活让他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