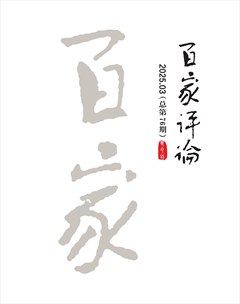内容提要:色彩与身体是海因诗歌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辅助诗人完成对个体经验和历史认知的表达。诗人以不同的观世视角,显示出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是倾心于描绘色彩,在对色彩的考镜源流中,看到社会形态与人类精神的发展演变,在回返本源的过程中,生产出一种在现存秩序下的惊觉与反思。二是专注于身体感知,在身体的拆解与化身结构中,净化自我,在现代社会返还自然秩序。三是将色彩与身体同时纳入文本,以绘画技法复活诗的隐喻功能,发现事物不可见之面目,在艺术融合中突破诗歌既有的美学规范与表达局限,拓展诗歌的意义空间。在人类精神困境频现的现代社会,这种源自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的诗思融合,是诗人走出精神困境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对新诗的发展命运充满考验的年代,以诗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市场化浪潮中逐渐失去主体地位,其所面对的精神困境是多方面的。现代社会中物质的过度膨胀导致的人文精神衰落,而新诗遭遇的边缘化命运,也注定给予诗人以重创。在精神困境之下,诗人作为先行的返乡者、民族精神的重建者,必然担负起重返人类精神家园这一使命。如何突破困境,重新发挥诗歌的有效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90年代诗歌试图从束缚中解脱,而选择向历史化迈进的时候,海因作为其中的一位,则开始向远古的人类文明寻求资源,其中色彩与身体是两个重要媒介,它们辅助诗人完成对个体经验与历史认知的表达。原始社会部落民族以色彩涂抹面部的行为,意在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感知基因,抵达自然秩序与结构。在创造人类社会的进程中,色彩与身体之间的自然联系逐渐割断,转化为其他形式延续下来,典型地表现在民俗仪式之上。在千百年的发展演变中,色彩与身体作为人体、自然、人类文明的综合体,具有崇高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特质。在自然秩序与社会伦理被迅速掩盖的年代,诗人以色彩与身体为履,在不断出走的世俗社会,意欲返回神圣的人类家园;在精神之根的照耀下,在秩序的重新排列中,实现对困境的突围。因此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人,海因实则是在反现代化浪潮下,将诗歌创作纳入时代发展与文化传统中,探索独属于中国新诗的艺术修辞与思想启示。
一、以色彩观世:脱胎于俗世的民间
中国传统“五色观”最初起源于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色彩膜拜,自然崇拜之下的色彩,将人与自然和宇宙统摄其内。《周礼·考工记》中载:“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春秋战国时将五色与五行学说相联系,于是色彩被赋予生命之意与社会意识形态。海因对色彩的痴迷是显而易见的,如《太阳和它的三堆颜料》《红》《蓝》《白》等,而他由色彩所传达出的思想观念则曲折隐晦。在海因看来,色彩并非仅是一堆颜料,而是一种高级形式。“色”指一切可见或不可见的事物和现象,而这些事物和现象是由因缘聚合产生,“空”是事物的本质,“有”从“空”中生。因此纯粹的色彩将世间一切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物都包孕其中,从而孕育出一种原始的、整一的、神秘的宇宙脉动。色彩谱系在诗人的不同创作阶段皆有变化,因此也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取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色彩与民俗活动之间的关系。原始宗教与色彩的联系,通过氏族图腾、等级观念、宗教礼仪等表现出来,其中原始仪式活动通过广布民间的民俗活动延续下来。诗人的考镜源流之法,使色彩显现出原始社会与世俗社会的象征意,与此同时将民俗活动所具有的世俗与神圣的双重性质,赋予民间社会。于是以色彩为始,海因诗歌中显现出一方脱胎于俗世的空间,而与之所共生的民众也显露出不可捉摸的人间幻象。因此海因诗歌中的色彩描述,实则关联着世俗社会中神话的民间生活与生命体验。
《蓝》这首诗是独特的,它以颜色为题,却并未描写颜色,而是首先将“蓝”指认为“马街书会”,这一流行于河南省宝丰县的传统民俗活动,是中国民间的曲艺盛会。若从视觉观感来看,“蓝”是马街书会中说书艺人的长衫大褂,而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蓝”则是代表中国民间或底层社会的传统色彩,诗人明确将其指认为神话片段,这与说书艺人百年来所讲述的神话传奇故事无不关系。由世俗社会中的马街书会所映现出的神话传说,以及祭神祈福仪式活动所彰显出的神圣性,使“蓝”生出它的色彩寓意一梦幻、深邃、永恒。由此,我们在马街书会中感受到“蓝”的神圣与静谧,正如诗人对民间生活的向往,对美好事物的思念。《高》是对距离和视角的描摹,却是通过持续升高的火焰来表现,由火引申出由原始社会延续而来的火崇拜。众人沉迷于燃烧的火焰,而这火则集中了红、蓝、白三色,在不同颜色的火焰中,显露出人的诸多欲望。从人类起源之时的敬祭于天,到逐渐发展的欲望沉迷,世俗社会在意义的不断消逝中,成为颓坏的人类文明的遗迹。
以色彩尤其是以传统五色为中心,生成的“火”“瓷瓶”“说书艺人”等诗歌意象,引申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原始的火崇拜、瓷器文明,以及传诵民族神话传说的说书艺术。海因诗歌中的色彩与意象具有穿透能力,承载着深厚的社会文化与人文精神,它们召唤出普通民众内在的社会文化记忆,同时又进入原始的文化记忆中去,以俗世之身召唤出神圣与灵性的光芒。然而在蓝色之外,还有一层模糊不清的灰色,因此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进入中心地带的朝圣者,同时也是远离故乡的漂泊的说书艺人,正如《高》中“有裂痕的瓷瓶”和“化为灰烬的火”,在生命绽放中已然蕴含着破碎与幻灭的因素,正如众生在火的欲望中沉迷,而众生没有名字,勾画出浓墨重彩而又忧郁晦暗的众生相。
这些相似意象在海因诗歌中发挥重要的结构性功能,“结构是以语言的形式展示一个特殊的世界图式,并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向世界发言的”①。这种意象叙事的生成,无疑是诗人的特殊构造。这些从远古时代延续来的民间之物,彰显出俗世民间的命运感的阴影,世俗的人与物,都笼罩上崇高的、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光芒,他们不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与物,而是被纳入历史与文化中去,成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如“升高的火焰”与“顶高的楼层”一般,以一种俯仰之间世间万物悉数在内的视角,将众生包裹其内。由此,在色彩与意象之间,我们看到社会形态与人类精神的发展演变,在回返人类本源的过程中,生产出一种在现存秩序之中的惊觉与反思,一种接近于澄明之境前的脉动与忧郁显现出来。海因准确地将他的色彩观念传达出来,空色关系所启示的宇宙本源与众生之相之间的幻化关系,已然昭示出诗人以色彩观世的真正含义。
二、以身体观世:在献祭中返还自然秩序
身体作为自然的产物,从诞生之初即拥有与自然合一的原初体验。而在商品拜物教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在各种人造装饰品覆盖的自然躯体上,人对身体的知觉体验渐失灵敏;另一方面,市场已然占据了自然秩序甚至社会伦理。“在这里,存在着现代化的最大的困惑:当人类生活与社会的各个分离部分日益理性化后,整体似乎日益地非理性化。”②海因致力于在日益混乱的现代社会,恢复人的知觉状态,用身体表现人类的原初体验和生命的本然状态,以期实现对混乱与非理性的调节。在海因诗歌中,身体是一切的界限,包括感官、情绪、思想等,以身体来认知世界这一诗歌创作理念的形成,与诗人洞察宇宙自然的运行规律与人类社会的真相无不关系,“一切经验都以肉体、以神秘的感官为基础。”③而诗人以身体为媒介所恢复的秩序与和谐,是历经世事之后所形成的人生体验与创作经验,其中或包含着顺从自然之心,或包含着不屈于命运之感。
(一)静穆的身体:观看视角下的客体化与知觉化
海因诗歌的生成主要来自生命内部的碰撞,而诗人却惯于将矛盾与混乱状态隐去,以观赏者的态度,介绍事物此刻的状态。一位好的观赏者,往往能发现事物的隐藏之美,而这便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观赏视角。在海因诗歌中,我们发现诗人常站于高处,以“广角的模式”来观赏事物,以便看清其整体面貌。正如温克尔曼在观看人体雕塑的背面时所描述的,“在这里我看到这一人体骨骼的绝妙构架,筋肉的来龙去脉,它们的分布与运动的基础;它们展开着,在我们面前就像在山巅能看到的伸展开的地势,在它上面,大自然显示了自己的无比丰美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