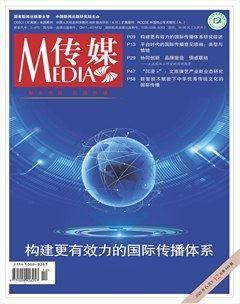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当前,文化传播不仅涉及文化内容,更事关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认同感。辩白式传播作为一种基于逻辑和理性推理的传播方式,试图通过反驳和澄清误解来恢复形象,是我们在舆论斗争中经常使用的传播策略。但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中,这种策略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尤其是在与西方文化体系的碰撞中,难以有效突破既有的负面偏见,甚至可能陷入“自证”的无限循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需要坚持战略视角、系统思维,在兼顾“辩白”与“共鸣”的基础上,以“共鸣”为主,通过叙事策略的转变,实现从“他者叙事”到“主体表达”、从“文化折扣”到“价值认同”的跨越。
一、辩白式传播的适用场景与困境
辩白式传播以澄清事实、回应质疑为核心,通过与对方辩论的方式,旨在减少或扭转误解。显然,这种策略因其理性分析、逻辑推理、证据支持等特点,尤其适用于针对时政类内容进行舆论斗争。然而,这种传播方式局限于回应性策略与“自证”陷阱,难以形成文化的深层共鸣。具体而言,辩白式传播面临以下困境。
(一)他者框架导致议程设置权让渡
“辩白”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以“澄清事实”和“回应质疑”为传播目标,本质上是一种被嵌入西方话语体系的
“应激性传播”—在萨义德(EdwardSaid)“东方主义”理论视域下,中国媒体被迫在西方预设的“他者化”叙事框架(如“人权危机”“威权威胁”)中进行有限回应,这种传播模式暴露了更深层的权力不对等。
被动应对的传播逻辑导致两个显著后果:一是陷入“他者叙事”陷阱,二是议程设置权旁落。心理学上的“逆火效应”表明,由于心理抗拒、事实幻觉与辟谣动机误解等原因,人们在信息纠正下,反而更加背离正确认知方向并强化对原信息的信任。与此同时,大量人力物力被消耗在回应西方媒体层出不穷的指控上,挤压了中方主动设置议题的空间,在西方媒体精心铺设的“自证陷阱”下,愈发偏离我们的核心叙事框架。
(二)单向传播导致文化折扣与受众疏离
“辩白”式传播往往不够重视对象国民众的文化语境,面临严重的“文化折扣”。这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导致。
一是符号化表达造成的认知壁垒。中国扶贫叙事中的红旗、标语等视觉符号,在国内高语境文化中承载着集体动员力、制度优越性等复合含义,但低语境文化背景的西方受众难以理解这些符号的深层内涵,甚至可能将其误认为“政治宣传工具”。
二是单向输出导致的互动缺失。“辩白”模式下,内容生产者往往急于从自身视角进行“自证”,从而陷入“传者中心”的桎梏。在传播中过于强调“我方叙事”,忽视受者主观能动性和文化背景,从而造成与受众的疏离。
(三)技术壁垒与平台依赖导致传播效能弱化
当前,国际传播的技术生态被西方数字霸权深度渗透,形成“算法偏见”与“平台依附”的双重枷锁。算法偏见其实是技术政治化(Technopolitics)的体现——平台通过“代码即权力”(CodeisLaw)的规则设定,将中国议题锚定为“次优先级”。例如,YouTube、Facebook等平台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等技术识别“敏感内容”,对中国媒体账号实施隐性限流,将含有“Xinjiang”“Tibet”等关键词的视频自动标记为“低推荐优先级”,让中国客观真实的声音难以广泛触达海外受众。在此背景下,算法偏见与平台规则成为“辩白”模式难以逾越的障碍。
同时,中国自主传播渠道受制于用户习惯壁垒与地缘政治打压,难以突破“平台依附”的路径依赖,导致传播效能持续弱化。目前,Facebook、YouTube等西方平台在全球社交媒体环境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较强的用户黏性。TikTok虽在部分区域取得突破,但需对抗用户长期以来的交互习惯,以及部分国家的封禁威胁。因此,我国自有平台建设存在“后发劣势”,在美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剿”和地缘政治工具的重重打压下,亟须以自主创新打破算法偏见、摆脱平台依附,建立以我为主的立体传播网络,重新定义全球传播生态。
“辩白”模式的局限性不仅源于传播策略的被动性,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国际传播权力结构和技术霸权的限制。跳出“解释一反驳”的循环,转向以价值共鸣为核心的主动叙事,或许可以有效突破当前困境。
二、从“辩白”到“共鸣”的国际传播范式转型
在对外舆论斗争中,“针锋相对”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时,必须有理有据有节地予以回击。但是在文化传播中,“针锋相对”往往难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更多的是需要通过文化浸润、价值传导、平等对话等方式,实现与目标对象的共鸣。
(一)转型的基础
在全球化叙事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际传播须超越信息单向输出,转而构建以价值共鸣为内核的传播范式:以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哲学根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文化内核,依托情感、利益、理念三大维度构建价值共鸣的传播范式。
1.文化内核:从“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不仅体现于儒家“和为贵”的伦理观,更贯穿于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实践。从古丝绸之路的商贸互通到郑和下西洋的和平远航,“和”文化始终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底色。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厚往薄来”的礼治原则,彰显“和”文化的实践基因。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