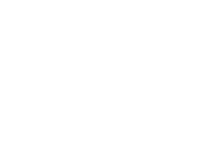谁也不会没事就捅自己几刀,除非不得已。
福建福州火车站应该还记得,1998 年第一家永辉超市开业时的锣鼓喧天。它肯定没想到这家超市自 2010 年上市后的 2021年就迎来了大亏损,惊人的 39.44 亿元。亏损像暮日西沉,27.63 亿元、13.29 亿元,直到连续第四年的 2024 年,亏损 14.65 亿元。
股 价 跌 到 2.08 元 的 时 候,“ 白 衣 骑士”也好,“门口的野蛮人”也罢,叶国富带着 62.7 亿元现金来了,一举拿下了永辉29.4% 的股权。曾缔造年营收 900 亿元的“超市之王”变换了大王旗。
2025 年 5 月 28 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发布公告,永辉超市董事长张轩松,因子公司 39 万元搬运费纠纷被“限高”。
39 万元,是永辉曾经不到一秒钟就能赚到的数字。世人惊诧 48 小时后,这场风波虽然停息,但还是将传统零售巨头转型的艰难显现了出来。
零售行业,特别是线下零售行业,这几年如马行薄冰。沃尔玛、家乐福等中高端、大型连锁企业经营受困,接连撤退 ;好想来、赵一鸣等新型社区折扣店又侧面截杀。叶国富掌舵永辉,像是临阵换将,开始了一场刀刀向内的杀法。
世上没有“一招鲜,吃遍天”的武功,如果有,那也经不起前赴后继挑战者们的车轮战。永辉一刀刀砍向自己,希望向死而生。决绝中的壮士断腕,是零售行业在传统范式中寻找新范式的一次革命。

大刀向成本上砍去
2 个月后再来永辉,看到这家经过“胖东来式”改造的新店,梁光(化名)最直观的感受是“贵了很多”“这很不‘永辉’”。
永辉曾经是“物美价廉”的代名词。1995 年,超市概念刚刚兴起,于东来在河南许昌种下胖东来的种子,张轩松则将一家 100 平方米、名为“古乐微利”的超市开进了福州鼓楼区的一个居民区。别人毛巾卖 3 元,他只卖 2.3 元。靠这种“微利”特色,3 年后,他就在福州火车站开了第一家以“永辉”命名的超市。
永辉彼时的刀,向上砍向麦德龙等国际巨头代表的高端商超,向下砍向遍布城市各处“脏乱差”的农贸市场。永辉“刀”的主要组成材料,就是成本,下刀处,直指生鲜品类。
生鲜首先需要本土化的专业人才,其次要理顺从产地到市场的环环渠道,或者,可以自建完整的产业链条,由产到销。不过,无论采取何种传统方式,不确定风险都实在太多了 :中间任何一级批发商都有可能违背合约、私调价格 ;中间任何一级仓储方都有可能以次充好、以少充多。正是这些来自本土、来自复杂人脉关系的困难,生鲜一直是农贸市场的主力,造成“大巨头”们热衷于主营相对规范的日用商品,把生鲜定位于“鸡肋”。
“只有改变才能求生存。”此时永辉规模尚小,便于在复杂的生鲜市场上掉转船头。张轩松决定剑走偏锋,调整商品结构,以差异化策略与巨头们区隔开,将生鲜经营面积调整到 40%,甚至是 60%以上。同时结合福州人买菜的习惯,首创超市六点半开门的奇景。
张轩松的战略很明确,主营生鲜,定位家庭主妇、上班族,既能避免与大鳄正面交锋,又能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这便是“农改超”的起源。
张轩松发现,“农改超”仅仅停留在“卖不同品种”的层次上,在渠道上却与其他超市、农贸市场大致相同,走“产地—采购商—批发商—超市采购员”的传统路线,超市里的生鲜 ,实际上经过了三批,甚至是四批,价格自然偏高。
如果是奉行“产地—超市采购员”的一级渠道,搞自营直采呢?
于是,张轩松着手建立了一支采购员队伍,直接与生鲜产地对接。这样一来,永辉价格优势已经超越竞争对手。在 2003年,福建大白菜采购价约为 0.22 元 / 公斤,到第一批发商升至 0.36 元 / 公斤,再到市内采购点,已升至 0.45 元 / 公斤……而定位于“微利”的永辉大白菜,超市零售 0.26元 / 公斤。
与采购队同步,张轩松在福州建立配送中心。这样,纷繁复杂的“供应商—分店”的交易关系,浓缩为“供应商—配送中心”的二元结构。各分店的外部联系也转化为连锁企业业务关系。这样一来,进货谈判数量呈几何级下降,交易费用、履约费用都大大减少。
此时,福州人发现,去永辉买菜,已经成为最经济实惠的选择,客流蜂拥而至,销售速度也大大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