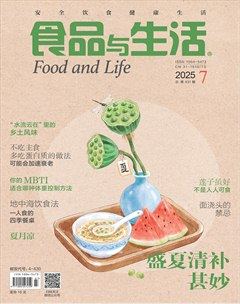以下, 是用味觉临摹的盛夏中国山水图,是不同民族在岁月长河里共同谱写的生存诗篇,能同时品出山林草木的芬芳与农耕文明的踏实。清补的盛夏,是诗和远方,每道菜肴都是山河的切片,每口热汤都翻腾着光阴的故事。
汤,是中国人的食疗精髓,讲究顺时顺候。 盛夏时节,冬瓜薏米汤祛湿,百合莲子汤健脾,均是消暑妙品。
广东人最懂“清补”二字,溽暑漫喉时,一盅清汤便能令三焦沁透。广府靓汤讲究药材与食材结合,喝汤弃料,汤能澄澈见底,药材与食材的鲜融到一处,很似潮剧里婉转的余腔,在舌尖缠绕。
我出生于上海,祖上广东潮州人,从小也耳濡目染这汤里的乾坤。记得儿时,每到伏天,家中灶上就不得闲:老鸽、童子鸡、排骨与各路参茸海味相互搭配,轮番登场。某年暑假,父母带我初至香港,在“丽苑酒楼”吃到一盅椰肉炖鸡汤,觉得那风味很独特,椰香清雅,党参微甘,杏仁含蓄,清甜中有股温润力道,暑气顿时消散三分。离港前夕,母亲又带我去上环采购汤料,德辅道西的老字号铺子里挤满山珍海味和中药材,长大后我才知道,那块地方过去叫“南北行”,是19世纪时期香港的金融贸易场,小说《胭脂扣》里,十二少就是南北行的富家公子。
后来我赴美读研,每到入伏,唐人街便是慰藉乡愁的福地。那里,许多挂着老匾的干货店和药材铺让我感觉恍若时光逆流,重返香港旧时。店里多是当地的华人盘桓,偶尔有洋客 闯入,茫然四顾如同看西洋景,终不得其道而出。老板见我打着越洋电话询问母亲煲汤事宜,知我是个生手,也热心地指点一二。纽约市规森严,活禽买卖绝迹。当时一位中学同学的外婆来陪读,人生地不熟的,竟在唐人街菜场里与摊主通得暗语,购到了活鸡,那真是异国他乡的一桩奇事。她兴奋地叫我们一众老友去家中品尝那碗现杀现炖的鸡汤,汤水清澈如故土的月色。
盛夏的补汤,未必都需文火慢煨。昔日胃口恹恹时,母亲也会做番茄猪肝汤来醒脾。她把番茄炒透起沙后添水,猪肝切薄片,裹淀粉, 往沸汤里一氽即好,口味酸甜。这汤看着简单,要把猪肝切得薄如蝉翼、味道鲜嫩爽滑,不仅考验刀工,对火候的把控要求也十分严苛。
水族之鲜也是消夏的妙品。谚云:“消暑吃鳝赛人参。”童年,我家住在上海的铜川路上,水产市场和曹阳菜场都近在咫尺。蝉声浸透黄梅湿气的小暑,我常随母亲去菜场买菜。那时我总喜欢看木盆里的鳝鱼游弋,鳞光暗涌,摊主的竹刀在鳝颈轻巧一划,黄鳝顺势褪下银甲,现出玉带白肉,此般市井之象一去不返,令我怀念。鳝筒汤配金华火腿片最鲜,母亲将鳝段与火腿一齐丢入锅中,缀以香菜,清雅脱俗。最险中求鲜的,当属西南山林的野菌汤。去年盛夏,我正怀着孕,师姐从云南寄来满满一箱山珍给我滋补——里头有鸡枞菌、青头菌、见手青,还有许多菌子长得奇形怪状,我和丈夫都叫不上名字,只得拿手机拍照后网络搜索。师姐再三叮嘱我“:一定要煮够30分钟,不然可能会‘见小人’。”此言一出,倒让惜命的我吃得有些忐忑。 那些天,家里整日飘着来自西南山林的清气,菌汤鲜得像把整个雨季的云雾都炖了进去。贵州龙里县有道名汤叫“肉饼鸡”,是将鲜菌、山鸡和用 猪肉糜压成的肉饼同煮,滋味鲜浓,层次丰富, 当地人还喜欢以此汤为底涮火锅。
今年家中新添了小老三,远在上海的母亲便迁来北京同住,帮我一起照顾孩子们。立夏才过,她拿出不久前从浙江诸暨山农那里购得的笋干,开始盘算起要做老鸭扁尖汤了。昨日醒来已是晌午,闻得满屋弥漫鸭肉和春笋的香气,见母亲在厨房里有条不紊地煲着汤,此情此景,仿若回到了20多年前的夏日时光……
文火慢煨至骨酥肉融,不显浊腻,喝一口,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
昂刺鱼豆腐汤也很美味。这鱼另名“黄辣丁”“黄颊鱼”“鲿鱼”,我到北京后,又知北方人叫它“嘎鱼”。昂刺鱼汤和鲫鱼汤的做法一致,想要得到乳白如浆的汤色,得先把鱼煎至两面金黄,倾入沸水猛煮后添嫩豆腐,出锅时撒一把葱花和胡椒粉,即成。
文蛤、蛏子与冬瓜、丝瓜和苦瓜都是消夏良配。上海人常做的丝瓜蛏子汤,清 甜鲜洁,令我百吃不厌。蛏子要先放在水中,滴油静养吐沙,焯水、去壳备用,随后丝瓜清炒,加水与蛏肉同滚,再往汤里沉几粒艳红的枸杞,汤色便如朱砂落素绢一般可人。福建有苦瓜蛏子羹,在汤中添发菜丝,勾薄芡,口感上多了一缕醇厚。 山东的汆西施舌,汤清如玉池,蛤肉舒展,
太河宴里的山水交响
文 | 袁殿文
一直没有来过辽宁本溪,恰逢这次出差,对本溪有了极为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