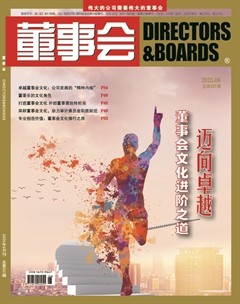从“定性”角度看,信披违规责任追究以上市公司具有管理可能性为前提;而从“定量”角度看,行政追责、民事赔偿、刑事追责需要审慎拿捏惩戒尺度,唯有如此,相关惩戒才能实现过罚相当
2025年3月1日,《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裁量基本规则》正式实施,其核心目的是规范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裁量工作,统一执法尺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裁量规则共有25条,虽做出精细化规范尝试,但鉴于中国证监会监管违法行为类型众多,因此其整体表述依然是较为原则性的。
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中国证监会的历年处罚中占比最高的信披违规为例,聚焦上市公司信披违规追责如何实现过罚相当。具体从三重管理维度展开:
其一,“对上负责”,明确上市公司对大股东的主动管理义务。对于大股东隐匿股份代持、隐瞒关联交易等行为,上市公司应意识到其对股权结构清晰性、交易对手关联性负有法定核查义务;反之,若上市公司仅作为履行形式审查义务的“信息通道”,则不应对其施加过重责任。
其二,“对下负责”,厘清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管控边界。例如在重组阶段,子公司作为独立交易方,由其导致的信披违规,上市公司或可免予连带责任;但并表后,上市公司则应担负起对子公司的财务监督责任。
其三,“对己负责”,探讨上市公司自身信披违规的惩戒尺度。行政、民事与刑事责任的衔接需以信披违规的实质重大性影响为锚——若违规信息未引发市场价量异动,则不应对上市公司过度追责。
对上负责——
在职责、能力范围内主动管理大股东行为
首先,对于大股东潜在的股份代持及关联交易,上市公司负有核查责任。关于股份代持行为,例如,在起某股份案中,2016年12月13日,起某股份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章某民和梁某进、吴某雅、王某助、庄某卿4人分别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章某民以每股5元的价格向上述4人转让其间接持有的起某股份股票合计2000万股,暂不办理过户,由章某民代为持有。起某股份在相关定期报告中对上述股份代持行为均未予以披露。在行政处罚申辩中,起某股份认为,起某股份原实际控制人章某民始终未将股份代持事项告知公司,起某股份不知情,也无从披露该事项,因此不应承担行政责任,中国证监会对此予以否认。
类似的,在奕某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挂牌时,股东霍某秀代替他人代持102.5万股,奕某信息未在申报材料中予以披露,被全国股转公司予以通报批评。公司申辩称,其不知悉股东霍某秀代持事项,但股转公司认为,奕某信息有义务确保其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在挂牌时未清理且未披露股份代持情况,理当担责。
关于关联交易行为,例如在南某新百案中,上交所认为,南某新百在相关公告中,未披露交易对方、标的公司与公司及控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未就前一次公司控股股东对交易标的母公司的股权转让属于代持做出披露,损害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南某新百认为,交易对方南京三某医疗从未告知其实际控制人马某治与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同时,公司在筹划收购徐州三某医疗股权的过程中,从不知悉股权代持关系。对此,上交所认为,南某新百应明确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产权、业务和资产等方面的关系,做出必要的尽职调查,仅以因疏忽而对关联关系和股份代持不知情的理由难以成立。
其次,对于违规增持或减持,监管部门通常不会对上市公司进行惩戒。例如在梅某吉祥、三某科技、中某软件等上市公司股东违规增持案件中,监管部门均只处罚了法人或自然人股东,由于上市公司并非相关案件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仅仅作为信披通道,因此并未被追责。
除此之外,一个更模糊的问题是,当上市公司作为大股东信披违规行为的受益者时,即使公司本身无违规的主观故意,是否应被追责?例如,2021年6月,金某泰公司发布公告称,其董事兼总裁袁某、控股子公司总经理罗某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总计不低于3亿元,中小投资者因此热情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