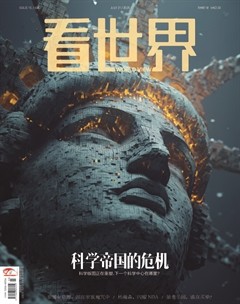特朗普政府和美国高校的矛盾,始终没有停歇。
最新的“大而美”法案,大大提高了高校捐赠基金投资收益的税率。最惨莫过于此前硬刚特朗普的哈佛大学,经历联邦拨款的冻结、停招国际生的威胁、对教职工和学生的政治审查、学术项目被叫停等一系列政治干预后,现在它顶着每年新增10亿美元税负的压力,不得不继续削减开支、继续裁员,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抛开双方的纷争,试想一个问题:没有哈佛的美国,将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其实哈佛比美国还要古老,成立于1636年,所谓“先有哈佛,再有美国”。哈佛是英国清教徒登陆马萨诸塞湾后创办的。彼时北美大陆是远离文明世界的荒野。清教徒们肩负开拓蛮荒、教化民众的重任,试图在新大陆建立一座道德楷模般的人间天堂,亦即“山巅之城”。哈佛,最早作为一座神学院,负责为殖民地培养神职人员、公职人员和各领域专业人士。可以说,以清教徒精神立校的哈佛,正是美国精神的化身。毕竟,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美国正是在清教徒的天职契约、禁欲主义、勤奋劳动和节制消费等新教伦理中,发展了自身的资本主义。
但也正因如此,到了19世纪中叶,哈佛仍是一座死板的、充斥机械式教学的教育机构,平庸到了极点。它长期以来被盎格鲁-撒克逊人把持,对犹太裔申请者持怀疑态度,大多数时间都将其他族裔拒于门外。这也像极美国自身—建国后一个多世纪,孤立主义都是历史主流。美国学者威廉·C.柯比(中文名柯伟林)在《思想帝国》一书中说:“一个持久繁荣的国家通常不会拥有糟糕的大学。”二战结束后,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奠定了全球霸权地位。而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一系列顶尖精英学府,则是这种霸权的基石—美国政府意识到,通过对高校的资助,美国可以引领世界创新。哈佛如今的地位,以及美国顶尖大学体系的优势,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根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美国15岁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科学方面,只能算“还不错”,处于国际同龄人的中等水平。但这显然不足以奠定美国科学的辉煌。两组数据说明一切:美国电气工程研究生有70%是外国出生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生也高达63%。可以说,美国整个STEM劳动力体系中,外国人和移民撑起了半边天。论成果,2000年以来,移民拿的诺贝尔科学奖数量,也占美国整体的40%。剥离美国所依赖的外国人才,美国科学将更像其K-12的表现—平庸,最多算个“还不错”。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美元霸权让美国获得了一种“过度的特权”,美国人得以过一种超出自身能力的生活。美国的科学特权,何尝不是如此?但现在,美国可能在颠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