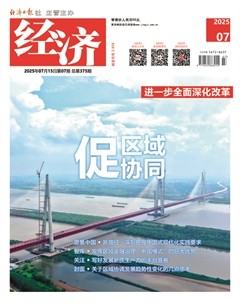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跨区域协同发展是实现全国范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支撑。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可以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要素流动的掣肘,实现区域优势互补与错位发展,形成梯度合理、布局优化、分工明确的现代化区域经济体系。近年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级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均以“协同”为核心目标,体现了国家对区域分工合作、功能互补的高度重视。跨区域协同不仅在经济层面意义重大,在科技创新、生态治理、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市场、统一治理,推动“物理连接”向“制度融合”转型,构建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格局,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跨区域协同的体制机制障碍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产业体系完善、创新资源集中,形成了对高端要素的强大集聚效应;中部地区和成渝都市圈、关中地区紧随东部加快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在提高对内对外开放进程中,加快形成要素和企业集聚,持续提升发展效率;西部部分地区和东北部分地区,虽资源禀赋优越、区位条件独特,但产业基础薄弱、产能结构偏向传统,发展能级不足,地区间差距呈现扩大趋势。长期以来,“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治理格局导致产业同质化、资源错配、生态压力加大,形成“各自精彩但整体低效”的格局。尽管近年来跨区域协同取得积极进展,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多方面体制机制障碍,成为制约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行政壁垒依然明显,地方保护主义尚未根除。当前,区域经济运行仍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财政分配、土地审批、招商引资等资源配置依然“以块为主”,导致地方政府注重本地利益最大化,跨区域协作动力不足。其背景是在财税分配、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医疗管理体制影响下,各自为政实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同时,由于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力量大于区域间资源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力量,相邻地区之间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阻碍了区域专业化形成,限制了地区间分工合作。
规划体系在上下联动与横向协同方面功能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在重大跨区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流域生态治理等方面,依然存在“政出多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交叉管理”的问题,不同区域空间规划、产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导致项目审批周期长、落地效率低。
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不完善,地方积极性受限。跨区域协同往往意味着一地付出、多地受益,现行财政转移支付与补偿机制尚不足以覆盖付出地区的成本,导致部分地区对生态保护、产业疏解、公共服务共建等缺乏内生动力。以生态保护为例,跨流域、跨省区的水资源调度和生态修复往往涉及下游受益、上游付出,若上游治理成本得不到有效弥补,地方推动协作的内生动力难以持续。
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不高,流动仍受制约。人才跨区域流动面临社保、户籍、教育等制度障碍,这与国内不同省份、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差异和社会保障能力方面的差异高度关联,而且具体的相关制度在实施方面也各有各的做法;资本跨省和跨区域开展企业并购重组和开展跨区服务都受制于行政壁垒、金融监管与审批体系等因素影响,技术与数据流动在目前监管体制和监管规则不完善的情况下,缺乏统一标准与互认体系,导致市场一体化水平不高,协同发展的资源基础薄弱。
跨区域治理体系和执行力有待提升。部分区域协调机构缺乏法定地位与执行权,合作平台尚未形成常态化机制,信息共享不足、执法协作薄弱,重大事项难以形成统一决策与行动,区域协作更多依赖行政推动,缺乏内在机制动力。此外,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仍以地方经济总量和增速为主,区域协同效应尚未充分纳入地方领导干部绩效评价,协同发展缺乏明确的考核导向和硬约束。
总体来看,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既有体制机制的深层障碍,也有治理能力和利益格局的结构性掣肘。破解这些障碍,需要进一步理顺中央统筹与地方自主的关系,完善顶层设计,创新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构建规划一体、政策协同、市场统一、治理联动的制度体系,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从“形式协调”走向“实质协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