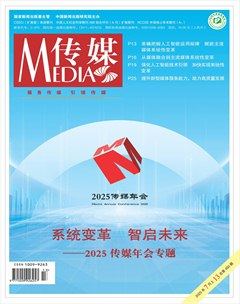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是对主流媒体新阶段改革任务的顶层设计,为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个改革的关键节点,2025传媒年会以“系统变革智启未来”为主题在江西抚州召开,汇聚学界、业界力量,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迭代并深度渗透媒体生产和传播全过程的背景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创新路径,对于传媒行业科学谋划发展、推动改革落实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作为业界代表,在该年会上从提升新型媒体服务能力角度,简要论述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价值逻辑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现将内容进一步整理,与读者分享。
服务型媒体的概念与意义
服务型媒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和阐述,源于笔者在2019年第十四届中国传媒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当时是媒体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五个年头,机构媒体围绕内容、技术、渠道、产品,在平台搭建、资源整合、流程改造、技术升级等方面持续和精准发力,内容生产力、媒体传播力有了明显提升,但媒体生产传播同质化和有效性两方面问题随之凸显。笔者基于光明日报社融媒体的实践探索,在传媒年会上提出“服务型媒体”概念,围绕以服务能力建设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工程,从媒体自身建设的层面和维度作阐述,希望在媒体融合面临体制机制、平台传播力和影响力瓶颈的局面下,提示机构媒体可以通过提供媒体服务,拓展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演讲内容后来整理成文,发表在《传媒》杂志上,题目是《增强服务能力,构建服务型媒体,推进媒体融合建设行稳致远》。
当时梳理的服务型媒体的概念是:服务型媒体是以媒体的内容生产、信息传播等能力为基础,将服务意识贯穿于媒体运转的全流程和各环节,明确自身的特色领域、主要受众,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能充分发掘优势资源,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提供高质量、特色化、多维度服务的新型媒体。笔者认为这一定义在当下依然适用。
此后,学界对“服务型媒体”这一概念有一定反应,甚至能看到有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将论述“服务型媒体的意义”设计为学硕招生题目,而给出的标准答案,除了笔者论文的几个要点外,还增加了一个很有逻辑的角度。
这里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改革任务,笔者想对“服务型媒体”从概念和逻辑上作一些升维,进一步论证主流媒体如何通过整合形成新型媒体服务能力,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新闻 + 政务 ⋅+ 商务 + 民生”等媒体融合发展模式备受关注。今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中国报业创新发展案例专家评审时,笔者发现,各地申报的运营模式创新案例中,有许多都属于此类,如报社组织团队承接品牌宣推活动、电视台组队开展电商直播等,并且申报表格中都列出了创收数目。这些无疑都是非常接地气的媒体服务项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这样的媒体服务项目在接受审计和专项巡视时,其创收的合法性会不会受到质疑。这说明提供媒体服务已不单纯是学术层面的话题,也成为媒体业界必须解套的难题,需要大家尽快凝聚共识,以便在实践层面据此建立规范化的制度框架。
提供媒体服务是主流媒体的核心职能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服务”并非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需要具备的新增功能,而是媒体本质属性的应有之意。比如,从早期报纸开设“读者来信”专栏,回应民生诉求;到广播电台设置“热线互动”节目,搭建与听众的沟通桥梁,再到电视台推出“民生新闻”板块和“电视问政”栏目,都是在关注社会痛点,服务属性始终内嵌于主流媒体的功能基因中。
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如今,主流媒体机构已不仅是信息资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更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这种角色的升维,要求我们将媒体服务能力的表述,更新为新型媒体服务能力,如此才能更为准确地概括当下媒体自身与媒体服务能力两个维度所呈现出的创新特征。
今天的机构媒体,不仅在内容形态和技术应用方面历经了多轮迭代一一从文字、图片,到短视频、直播,从大数据算法推进到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内容,媒体的传播载体与技术工具持续升级;其自身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完成了从“传播者”到“服务者”的升维,具备了整合社会资源、破解治理难题、引领文化生态的综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