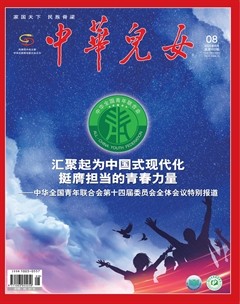环保不能只靠热情,还需要专业,需要创新,更需要机制保障”
在阿塞拜疆巴库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现场,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微微欠身,用带着湘音的普通话向世界讲述中国湖南民间环保组织的实践。
当洞庭湖越冬候鸟群飞的画面与湘江两岸的绿意交织,这个从资江源头走出来的湖南汉子,正将中国基层环保的故事,播撒向更远的世界。十九载逐绿之路,从洞庭湖畔的“湿地使者”到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声音,何建军的足迹里,藏着一部湖南民间环保的成长史。
少年与大自然的约定
1987年,何建军出生于湖南资江源头的一个小山村。“我们湖南是‘一湖四水’,我家就在‘湘资沅澧’的资江源头。”他总爱骄傲地向人介绍:“我的家乡拥有湖南第二处世界自然遗产地——崀山,‘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就是诗人艾青在我家乡写的。”他常常提起家门口那条清澈的小河,河水最深不过两尺,却足够让一群小孩在其中消磨整个夏天。与山水为伴的童年是他内心深处最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的河水很清澈,捧起来就能喝。”何建军回忆道:“每年夏天,我和小伙伴几乎整天泡在水里,翻螃蟹、捞小鱼。傍晚回家时,竹篓里总能装上半筐小鱼小蟹,爷爷奶奶用红辣椒一炒,就是最鲜美的晚餐。”
最让何建军难忘的还有“凉粉果”——一种野生凉粉籽,揉搓出浆后,盛在不锈钢盆里,放进山洞冷藏,几小时后便凝结成晶莹剔透的“山野果冻”。“现在的孩子吃的是工业果冻,我们那时候吃的,是真正的自然馈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偏远山村,电视还是稀罕物,孩子们主要嬉戏玩耍的地方就是大自然。“在大自然中长大的孩子,胆子自然会大一些。我们小时候常常赤手爬到三四十米高的树上摘野果,这些经历都是现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不敢想的。”
很多年后回望,童年与自然亲密无间的相处,无形中在何建军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而家族精神传承的力量,则是支撑他行远路不辍的内在源动力。同村的表伯是个木匠,每次到何建军家做木工,空闲时就会给小建军聊家族往事。从木匠表伯那里,他第一次知道高祖是家族的族长,清末时期家族昌盛,高祖在当地一带德高望重,不仅操持着家族大小事务,还积极修桥补路、兴办私塾,乐于为邻里乡亲排忧解难,倍受尊敬。少年何建军听得热血沸腾。
后来,何建军有机会跟着爷爷去修族谱,也常常听到老人们谈起很多关于高祖的故事,高祖乐善好施、为当地作的贡献至今被家乡人津津乐道。家族故事对少年何建军产生了很大影响。家族先辈们的善举和威望,成为他生命中无形的指引,让他渴望能像他们一样,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样的教诲像一盏明灯,为他日后投身环保公益事业埋下了伏笔。
湖南环保公益职业化的首批践行者
2006年,何建军考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成为一名大学新生。在梧桐叶簌簌下落时,他看到了“绿源”环保协会的招新展板。何建军的目光被牢牢吸引。那些洞庭湖的照片里,既有他魂牵梦绕的浩渺烟波,也有触目惊心的污染现场——干涸的湖床、死鱼遍布的排污口、候鸟在“迷魂阵”中挣扎的身影。“加入协会能去洞庭湖吗?”他问招新的学长学姐。得到师姐肯定的答复后,他加入了“绿源”环保协会,这成了他环保生涯的起点。
何建军对洞庭湖有着特殊情感。他高中时喜欢背诵古诗词,尤其范仲淹笔下八百里的壮阔景象——“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无数次在他脑海中翻涌。
可是,当何建军真正走到湖边,洞庭湖泛着诡异的黑褐色,近岸处漂浮着塑料袋和死鱼,远处,密布的“迷魂阵”渔网像蛛网切割着湖面。眼前的一切让他痛心疾首。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成了周围工厂的排污池,范仲淹笔下的浩浩汤汤已不复见,被一片片杨树取而代之。何建军蹲下身,指尖触碰湖水,黏稠的触感让他联想起家乡那条被矿渣污染的小河。
童年清澈见底的小河随着上游矿产的开采,河床逐渐被冲洗下来的矿渣抬高,水位下降,溪水变得浑浊,鱼虾减少。“有一次春游,与几个小伙伴走到矿区,发现矿区附近河流里的石头全被染成了铁锈色。”何建军说:“那时候不懂环保,只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失去了一个老朋友。后来,失去生机的小河没有了小朋友的嬉戏声。”
彼时的何建军对“环保”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很朴素,直到接触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社区共管项目,才真正打开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