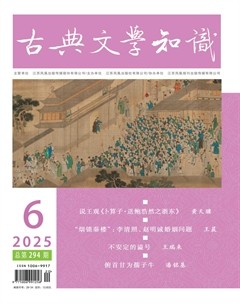公元前685年,在通往齐国的两条驿道上,飞奔着两支披麻戴孝的队伍,冲在最前面的是两位齐国的流亡贵族——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策马紧随其后的是他们的师傅管仲和鲍叔牙。这两支分别从鲁国和莒国出发的马队,与其说是在日夜兼程地奔丧,莫如说在争分夺秒地奔赴王权。彼时,齐国国政已是一片混乱,弑君篡位的公孙无知刚刚即位不到一年便被人所杀,形成了一个诱人的权力真空,作为这个权力真空的最有力争夺者,同为一母所生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仅进行着时间的竞赛,同时也在进行着心智的较量。快马加鞭的小白显然跑得太急了,一路上他只听风声过耳,绝对没有想过林中会有一支暗箭射来。这是直取心窝的致命一箭,施射暗箭的不是别人,正是公子纠的师傅管仲,他把对主公的忠诚涂抹在箭尖,一心要将公子小白射落马下。而历史总是在偶然与必然中行进,利箭射断了小白的铜制带钩,并没有造成致命一击,而小白则将计就计,咬破嘴唇,口含鲜血,佯装落马。黑暗中的管仲悄然复命,而公子纠在得到“捷报”后便明显放慢了奔赴齐国的脚步。这是一场谋略的比拼,当公子小白星夜赶至齐国,摇身一变成为齐桓公的时候,迟到者的下场已经不言自明。此时,一身盛装的齐桓公早已将胸前的带钩换成了美玉,但金属撞击的声音依旧是这位新任国君的梦魇。于是,处于兵车之围中的鲁国被迫杀公子纠以谢齐桓公,而刺客管仲则被关进囚车,押解至齐国。
对于已沦为阶下囚的管仲,齐桓公一心想要将之剁成肉醢,烹而食之!然而,最终让盛怒的齐桓公冷静下来的却是齐相鲍叔牙的一声耳语:“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史记·齐太公世家》)鲍叔牙说这句话时,声音低沉到只有齐桓公一人听清,但此后的2700多年间,这句话却有如黄钟大吕般响亮。与管仲私交甚笃的鲍叔牙完全可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国重臣,但为齐国霸业计,他却力荐管仲与之共辅国政,千载而下,此种胸怀绝非常人所能及。对于鲍叔牙此举,后世史家均不惜笔墨,“管鲍之交”由此脍炙人口,但史家在对鲍叔牙极尽褒扬的同时,好像都有意无意地对齐桓公轻描淡写。事实上,一条建议被采纳与否,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一国之君,更何况这建议还是一个与自己有着一箭之仇的刺客提出的!此时的管仲对于齐桓公而言,是欲杀之而后快的囚徒,更是助己成就霸业的股肱之臣,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当齐桓公最终将一脸怒色化为满面春风,并亲自打开囚车,拜管仲为上卿,我们看到了一代霸主的胸襟。
齐桓公以德报怨,管仲也不负众望。在管仲的力推下,齐国率先在各诸侯国间实行了国野分治之法,一改齐国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在军事上,他雷厉风行地推行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充足的兵源;在外交上,管仲创造性地提出“尊王攘夷”的谋略,即拥护周王室,带头抗击北方狄人和戎人对中原各国的侵扰,而彼时的西周王室已经衰微,齐国率先举起“尊王”的大旗,便能借周天子之命,号令各路诸侯。管仲的一系列富国强兵之举,深得齐桓公赏识,他诚恳地尊管仲为“仲父”,甚至向群臣宣布:“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所有施行,一凭仲父裁决。”而管仲也确实不负“仲父”盛名,公元前651年,“葵丘会盟”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次会盟中,各诸侯国在齐国的召集下相会于葵丘,周天子也派代表送来了贺礼并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至此,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
正是这“一箭之缘”,成就了管仲的治世之才,也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主之位。受到管仲的影响,齐桓公即位伊始,就将重用人才摆在了重要位置,《韩诗外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齐桓公见小臣,三往不得见。左右曰:“夫小臣,国之贱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见,其可已矣。”桓公曰:“恶!是何言也!吾闻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贵,不轻身于万乘之君;万乘之君不好仁义,不轻身于布衣之士。纵夫子不欲富贵,可也,吾不好仁义,不可也。”五往而得见也。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齐桓公的人才观很清晰:布衣之士如不求富贵,就不必委身万乘之君;而万乘之君如不好仁义,也不可能尊重布衣之士。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当然了,即便那位他三次拜访而不得的“小臣”不企求富贵,作为万乘之君的他也不可不尚仁义。最终,这位“小臣”还是被齐桓公的诚意打动,在齐桓公第五次去找他的时候终于同意见面。
可以说,礼贤下士是齐桓公让朝堂得以人才济济的前提,而他在管仲的劝谏下,一改奢靡之风,更为齐国的发展注入了满满的动力。史载,齐桓公曾颇好穿紫衣,结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国人纷纷以穿紫衣为时尚。然而,一件紫衣的造价却不菲,齐国举国皆尚紫衣后,紫衣价格高涨,五件素衣才抵得上一件紫衣。管仲听说后,力劝齐桓公带头不再穿紫衣,并且要对大臣中尚紫衣者表示厌恶,对不穿紫衣者表示赞扬,这样才会扭转国民尚紫之风。齐桓公深以为然,很快就带头不穿紫衣了,并且颁布了“禁紫令”,昂贵的紫衣不再流行,不仅平抑了物价,同时也形成了举国上下的节俭之风。
如果说齐桓公在延揽人才上的不拘一格、衣食用度上的节俭自律,让齐国得以国泰民安,稳健前行,那么,其在军事上的加强武备、夯实国防,则让齐国得以笑傲群雄。在各方势力此消彼长的群雄割据时代,齐桓公采纳管仲之言,率先在列国之前建起长城。彼时,管仲的改革,已使齐国国力强盛、成为东方大国,又先后灭掉了纪、谭、莒、莱等诸国,使齐国的地域扩展到东方海滨,逐渐消除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因此,齐桓公将战略防御重点转向南邻的鲁、楚,西南的卫、晋、宋以及北邻的燕国。为了达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目的,齐桓公在原有城墙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建。正是依托这项在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浩大军事工程,齐桓公得以坐稳春秋霸主之位,为齐国开疆拓土、防御入侵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支撑。当然,齐长城的建设并非一日之功,绵延千里的齐长城也不能记在齐桓公一人头上,但作为“中国长城之父”、作为比秦国东长城早了150年左右的大型军事防御工程的重要决策者,齐桓公已然在逶迤绵延于齐鲁大地的齐长城上,书写下属于自己的荣光!
如果给管仲更多生命的时日,最终君临天下的人真的很难说就是秦王嬴政;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当管仲油尽灯枯,走到生命的尽头,齐桓公的霸业雄图也宣告终结。昔日那个复国图强、求贤若渴的公子小白正在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骄奢淫逸的昏君,而随着惰性的增长,这位春秋霸主眼中的用人标准也开始在发生着改变。昔日忠心效命的管仲已经步入老境,尽管齐桓公还在一声声地叫着“仲父”, 但语气中显然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诚恳和热情,相比之下,一班奸佞小人的阿谀奉承之辞反倒成为齐桓公每天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正是这样用人标准的嬗变,让齐桓公时代出现了两个极端:国祚肇始之年,“管鲍”二人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令后世君王每当朝中无贤,便思管鲍;大厦将倾之日,一班奴才富于创意的表演则成为后世奸佞无法超越的“标杆”。你能想象出烹食婴儿的滋味吗?当齐桓公品遍百味,自叹“惟蒸婴儿之未尝”时,身为庖厨的易牙立刻烹熟自己的长子献给主公。你愿意为了成为一名近侍放弃男身吗?当竖刁手握烧红的刀子将自己阉割,我们看到的不是一脸沮丧,而是无比的兴奋。你能做到多少年不归乡看望父母?卫开方给我们的数字是十五年,他效忠齐桓公十五年没回过家,甚至父母去世也不回国奔丧。众小营造出一个无比“忠诚”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用人目光早已经迷离的齐桓公没有理由不酩酊大醉,而正是这种沉醉,最终酿成了一个王朝的灭顶之灾。
史载,管仲弥留之际,齐桓公曾亲赴病榻请其推荐继任者。对于齐桓公提出的易牙、竖刁、开方三个人选,管仲的目光是如此无奈:杀子以适君,自宫以适君,背亲以适君,非人情,不可。这是管仲给齐桓公最后的忠告,然而,这些忠告随着管仲的去世淹没在一片甜言蜜语之中,继管仲之后,易牙、竖刁、开方三人开始把持朝政,成为弹冠相庆的齐国新贵。包藏着祸心的“忠诚”迟早会变成国家的灾患,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正是这三人,将刚刚强大的齐国重新带入了一个拉帮结派混乱不堪的局面;而此时,身染沉疴的齐桓公已经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阴森的宫门被十几道铁锁紧紧锁住,齐桓公奋力的呼喊声慢慢减弱成为无望的呻吟,一代霸主最终在病饿交困中死去。“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史记·齐太公世家》)六十七天过去,当宫人们打开紧锁的宫门,看到的是一副凄惨悲凉之象:成群的蛆虫爬满了散发着臭气的尸身,一块素巾覆盖住一颗溃烂的头颅,面目,已成为齐桓公黄泉路上最不想带走的东西。
三往何劳万乘君,五来方见一微臣。微臣傲爵能轻主,霸主如何敢傲人。
——周昙《齐桓公》
曾写下大量咏史诗的周昙,单独为齐桓公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歌,而这首诗所关涉的,正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齐桓公礼贤下士的故事。世事如白云苍狗,成亦用人败亦用人的齐桓公已经化为了湮灭于齐鲁大地上的一抔黄土。如今,齐长城作为见证齐国兴衰荣辱和华夏民族历史变迁的重要物证,依旧如同一条巨龙绵亘在齐鲁大地之上,它西起济南,东达青岛,穿越了济南、泰安、淄博、潍坊、临沂、日照、青岛等城市,将黄河、泰山和浩瀚的大海连缀成一条沧桑的历史曲线,而在这段被誉为“中国长城之父”的齐长城上行走,我们除了可以在黄石关听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原山国家森林公园齐长城遗址感受到天然氧吧的惬意,还应当去抚摸它的残垣断壁,坐望它的岁月烟尘,至于2700年前那个在此湮灭了治世荣光的齐桓公,更应成为我们去探访齐长城时,必须走近的历史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