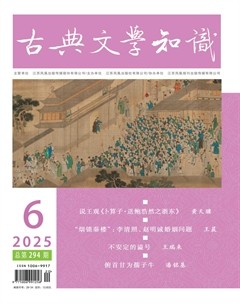一
齐梁时代连续产生了刘勰(466?—537?)《文心雕龙》、钟嵘(467?—519?)《诗品》和萧统(501—531)《文选》,这三部大书在中国文学史、批评史上全都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三部书分属两类,《文心雕龙》和《诗品》乃是理论批评专著,而萧统《文选》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作家,过去往往习惯称为“总集”。意外的是《隋书·经籍志》把这三书全都著录于集部的“总集”类,列为该类之首的挚虞《文章流别集》也是一部包含多种文类的文学作品的选本。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隋书·经籍志》“总集”类的小序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据此可知《隋志》“总集”类固然以前后各种“采摘孔翠,芟剪繁芜”的作品选本为主要对象,同时也将“解释评论”的专著,即后来称为“诗文评”亦即文学批评的著作也安排在这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诗文评类》叙曰:“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可见在唐朝的初年(《隋书》修于此时),“诗文评”一类的书因为数量较少,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于是便附列于总集之内。因为这些著作中所评说的作家作品范围较广,情形与总集有某种类似。
文学批评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也曾出现过曹丕《典论·论文》那样的专论,但一般情况下都在口头上进行,稍后才被记录下来,一直到晋代仍是如此,《世说新语》一书中即多有记载,这样的文学批评不免带有某种偶然的私人的性质。比较正式的包含批评见解的举措则是编撰作品总集(选集),把优秀的作品编选成书供大家学习参考,而选家评论的见解也就寓于其中了。出现得最早的选本大约是杜预的《善文》,其书名就是“好文章”的意思,此书自然也表达了杜预文学批评的见解。《善文》后来失传,传世者以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为最早。
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从事文学方面的理论批评,往往同指导人们欣赏名作、学习写作联系在一起。萧绎说得好:“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金楼子·立言》)可见当时编撰选集(总集)的主要任务乃是给读者提供写作的样板,这样的选本出于“品藻异同”的批评家之手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大抵重事实、重经验、轻体系、轻抽象。孔夫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大抵是从具体的作品批评入手,脱离文学文本、脱离创作实际的抽象理论非常罕见。文学选本之风行,根据正在于此。以选录作品来表达评论的见解才能“深切著明”。中国古代的选家就是理论评论家。
按文体进行文学之历史的与理论的评论研究,先前的选家如西晋人挚虞(?—311)早已在《文章流别论》中做过,稍后另一位选家东晋人李充(生卒年不详)在他的《翰林论》中也曾经做过。二者都是作品选,其中皆附有批评性、理论性的说明,这就为刘勰、钟嵘二家开辟了先路。
《文心雕龙》一书十分注意研究文本,该书“论文叙笔”的内容见于第六至第二十五篇,这里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其中“选文以定篇”正是选家的本行业务。把刘勰选定的各篇编排起来,就是一部刘氏的文学作品选。钟嵘在《诗品》一书中将他看好的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给予简要的评论,全书的序言则深入地探讨了若干理论问题。《诗品》原书中很可能是带有选篇的,这一部分失传以后就只能看到他的评论了。这种情形很有点类乎《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都是失去了原有的选文部分,只留下了评论。如果把今本《诗品》中提到的名篇名句加在一起,也就可以窥见钟嵘心目中一部历代诗歌选的大概情形。
可以说早期的选家挚虞和李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正是刘勰、钟嵘的先行者。所以《隋志》将“诗文评”方面的著作附列于总集之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后来以史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总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道理亦在于此。
萧统主持编选的大型文学选本《文选》除了一篇不算很长的序言之外,没有发表更多的理论批评见解,这是它不同于《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的地方,这里完全凭借所选的七百多篇作品来发表意见,影响读者,这个手段亦复甚妙。鲁迅先生说:
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鲁迅全集》第7卷)
鲁迅认为优秀的选本往往比理论批评专著更有读者,更有影响,这是一个深刻的观察。即以齐梁三书来说,《文选》影响最大,早在唐代即已注家蜂起,读者极其广泛,为《文心雕龙》和《诗品》望尘莫及。唐代以后,仍然是《文选》影响最大。钱锺书先生曾经指出:“昭明《文选》,文章奥府,入唐尤家弦户诵,口沫手胝……正史载远夷遣使所求,野语称游子随身所挟,皆有此书,俨然与儒家经典并列……词人衣被,学士钻研,不舍相循,曹宪、李善以降,‘《文选》学’专门名家。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叁焉。”(《管锥编》)研究《文心雕龙》的所谓“龙学”以及对于《诗品》的探讨近年来虽然也相当繁荣,但同“《选》学”之盛况相比,仍觉稍逊一筹。
二
《文心雕龙》《诗品》《文选》这三部大书都产生于南朝的首都建康,即今南京。
刘勰出生于著名士族东莞刘氏,但他所属的一支后已破落。这位青年才俊长期生活在建康,先是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萧梁建国后刘勰很快出仕,“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梁书·刘勰传》),这时东宫的太子正是萧统。萧统去世(中大通三年,531)后,他回到了定林寺,剃度出家,不久就死在那里。
《文心雕龙》一书的写作时间,一般认为在萧齐的末年。此书评论作家作品基本上迄于东晋,刘宋时代的情形亦偶有涉及,而称齐代为“皇齐”,不作任何具体的批评,采取回避的态度,这种情形表明此书当作于齐代。但书中也有些梁代的痕迹,例如很生硬地不用“衍”字,显然是欲避梁武帝萧衍的名讳。这应当是入梁以后作了必要的改动,并不影响此书撰写于齐末的基本事实。撰写《文心雕龙》时刘勰一直居于首都建康。
钟嵘也是长期生活在建康。他的父亲钟蹈官任齐中军参军,他本人在十五岁左右就入了国子学,并很快得到国子学祭酒(相当于校长)、著名作家、学者王俭(452—489)的赏识,推荐为本州秀才,稍后出仕为南康王萧子琳的侍郎,进入了上层政治文化圈子。萧子琳是齐武帝的儿子、竟陵王萧子良的弟弟,永明八年(490)被封为南康王。作为他的文学侍从之臣,钟嵘得以有机会与当时聚集在竟陵王西邸的大批文人建立了相当的联系,为他后来从事《诗品》作了重要的准备。在本书序言中钟嵘介绍自己撰写《诗品》的缘起道: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刘士章就是刘绘(458—502),《南齐书·刘绘传》云:“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时人为之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由此颇可考见刘绘当时以善谈著称。钟嵘因为与诸位“文章谈义”之士相交接,信息甚广,思维活跃,为日后撰写《诗品》准备了机运。
竟陵王西邸是著名的“永明体”的摇篮,周颙(441?—491?)是其中提供语音学理论的重要人物,他的《四声切韵》为诗歌运用声韵学的新发现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与周颙一起热衷于研究声韵的著名人物有王融(467—493),永明中钟嵘与其人有些交往,《诗品·序》中曾特别提道: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脁、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钟嵘对于永明体倡导者的基本主张并不赞成,但这种交往显然能够促进钟嵘更深入地考虑诗歌创作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当年的热门话题。《诗品》的酝酿虽早,成书却比较晚,但在天监十六年(517)以前应当已经完成。在这许多年中,他多半住在首都。
萧统作为当朝太子,更是基本不出首都,《文选》完全产生于今天的南京。萧统的品德和能力在史书中都得到很高的评价,但他最后却于无意中得罪了父皇萧衍。萧统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是在惭慨恐惧中度过的,不久更出了一场意外,匆匆去世。《南史·昭明太子传》载,中大通三年(531)“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诫不言,以寝疾闻。武帝敕看问,辄自力手书启。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动股”大约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萧统隐瞒病情应当是担心此事可能危及自己的太子地位,而结果耽误了治疗,以至于一病不起。中大通三年(531)四月,萧统去世,年仅三十一岁。
定林寺在建康近郊的钟山,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和梁王朝的东宫都在建康主城区,“后池”就是今之玄武湖。南京具有悠久而光辉的文学历史,近年来被评为世界文学之都,无论说古道今,皆属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