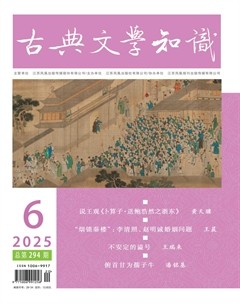《津阳门诗》是晚唐诗人郑嵎于大中五年所作的一首百韵长篇史诗,以华清宫及明皇故事为依托,展开安史之乱前后大唐兴衰之变的宏大画卷。此诗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其中的自注,共32处2237字,体量堪称唐诗自注之最。而所谓诗歌自注,就是诗人对其诗作的自我阐释,具有扩充诗歌信息、辅助诗情诗旨表达的作用。以位置为划分依据,唐代诗歌自注可分为四类:位于诗题当中的题中注、紧随诗题之后的题下注、位于诗序中的序中注以及出现在诗句之后的句下注。就《津阳门诗》而言,其32处自注均为阐释句意的句下注,覆盖诗句达125句,占全诗篇幅的62.5%,百字以上的长注有5条,最长者为190字,在唐诗自注中绝无仅有。
《津阳门诗》两千余字的绵密自注是诗人叙史论史的重要手段,也是诗歌文本中史实书写与评判的延伸,因此贯穿了强烈的历史意识。就该诗自注而言,其历史意识的表达可括为三点:
首先,重视史料文献的征引利用,既充实了诗歌中的史实叙述,也反映出诗人言必有据的严谨态度。与《津阳门诗》相类的唐代长篇史诗有8首,分别是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韩愈的《永贞行》、元稹的《代曲江老人一百韵》《连昌宫词》、杜牧的《杜秋娘诗》以及韦庄的《秦妇吟》,其中使用自注的仅有《连昌宫词》和《杜秋娘诗》。
元稹《连昌宫词》中自注只1处:“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累日之后,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关易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玄宗遣高力士大呼于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王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未尝不悄然奉诏,其为当时所重也如此。然而玄宗不欲夺侠游之盛,未尝置在宫禁。或岁幸汤泉,时巡东洛,有司潜遣从行而已。又玄宗尝于上阳宫夜后按新翻一曲,属明夕正月十五日,潜游灯下,忽闻酒楼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骇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诘验之,自云:‘其夕窃于天津桥玩月,闻宫中度曲,遂于桥柱上插谱记之。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谟也。’玄宗异而遣之。”此注由念奴善歌,众人悄然听之与李谟善笛,暗记上阳新曲而奏两部分内容组成。有关念奴善歌的文献记载共有9处,分属以《连昌宫词》自注以及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为代表的两个故事版本。有关李谟善笛的记载约30处,其中仅1处与《连昌宫词》自注的故事版本相同,即张祜的《李谟笛》诗:“平时东幸洛阳城,天乐宫中夜彻明。无奈李谟偷笛谱,酒楼吹笛是新声。”后人对此诗末两句的注释基本照搬了《连昌宫词》自注的相关内容。综而言之,传世文献中虽不乏对念奴歌与李谟笛的记载,但与《连昌宫词》自注的故事内容属同一系列者,均由之而生。
《杜秋娘》诗有2处自注,一处为“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句下注“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李锜长唱此辞”;另一处为“金阶露新重,闲撚紫箫吹”句下注“《晋书》:盗开凉州张骏冢,得紫玉箫”。该诗为开成二年秋末,杜牧入宣州幕府时途经金陵,重遇曾为浙西节度使李锜妾室的杜秋娘,感其穷老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