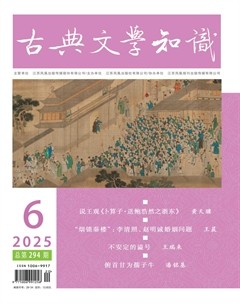元丰七年(1084)六月底,苏轼从黄州出发的行船抵达金陵,即将奔向下一个谪居地汝州。而此时王安石从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被罢相,彻底结束政治生涯,隐退江宁半山园也已经8年了。此时,王安石与苏轼在政坛上的强弱之分已经结束,两人一度针尖对麦芒的矛盾也烟消云散,同是政坛边缘人,没有了直接的对抗,剩下的也就是惺惺相惜了。
苏轼虽然在落魄之中,但一举一动仍备受关注。王安石获悉苏轼路经金陵,很想见一见当年的政治对手苏轼。已经64岁大病初愈的王安石穿着很朴素的衣服,骑着驴到船上来看望49岁的苏轼。我们原本以为的“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场面没有出现,而代之以两颗心的直接靠拢和无痕交融。
苏轼看到穿着便服的王安石走来,自己连官帽也没来得及戴上,赶紧迎上去作揖说:“在下苏轼今日斗胆穿着便装来迎接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这些官场的礼节哪里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设的呢?”王安石说得云淡风轻,没想到苏轼接着说:“这个在下也知道,礼是宰相门下的事情,我哪里能享受宰相门下的待遇!”苏轼这句话有点酸,但酸得有力度,大概也是他心里一直的想法,当着王安石的面说出来,好像是有点冒昧,倒是体现了对当年纷争不再介怀的淡然了。但其实,苏轼也在致王安石信中明确说过“某游门下久矣”(《与王荆公》一),只是此时可能忘了曾说过此话矣。
苏轼这话,王安石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说王安石门下没有苏轼的位置,当年确实如此,但怎么给苏轼留位置呢?当年苏轼这么激烈,冲锋在反对新政的第一线,王安石即便留了位置给苏轼,苏轼也不会来的。所以王安石只是笑笑,这一笑算是对当年两人尖锐矛盾的和解了。随后王安石说:“不说这些没用的了,我们一起转转蒋山如何?”蒋山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紫金山。
那一段时间,他们一起在山中转悠,也一起饮酒谈禅,好像金陵夏季的炎热也在这种平和的心态中清凉了下来。此前王安石与苏轼虽然在朝廷也经常碰面,但话不投机,根本没有机会深入交流,这次连续好多天在一起,深刻感受到苏轼的格局。王安石不禁感叹说:“像苏轼这样的人物,也不知道几百年才能出一个。”我不知道苏轼是否当面听到这句话,但如果听到曾经的对手能这样评价自己,大概也很欣慰了。而苏轼对王安石最近这段时间“存抚教诲,恩意甚厚”(《与王荆公》二),有了更多的触动。
据说王安石力劝苏轼定居江宁,苏轼应该是动心了,一度真的想在江宁买田,在钟山终老。但事实上,苏轼正在去汝州的路上,不过停下来与王安石快晤几天,即便有这个打算,也只能是以后再说了。王安石曾经赋诗《北山》说: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北山也就是蒋山,是王安石邀请苏轼同游的那座山。从蒋山上到池塘边,大片的绿色绵延不绝。无论是笔直的沟渠,还是弯曲的池塘,在阳光下都泛着迷人的光泽。在青山与绿水之间,王安石久久地坐着,享受着天地自然之大美,他数着眼前一瓣一瓣的落花,沿着芳草布满的小路边走边看,大概是总被美景所吸引以至于总停下脚步,回到家都很晚了。这首诗写出了王安石人生“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之后的闲适。这哪里还看出一点当年变法时期王安石那种自信和勇往直前的性格呢?看到的就是一个在青山绿水之间悠哉游哉的老人而已。
苏轼在这一年年底作了《次韵荆公四绝》,我们看第三首: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在诗中回顾了王安石当初从荒凉的山坡上骑着驴远远地走过来的情形,那种颤巍巍的苍老与无力感,一下子惊到了苏轼。因为此前苏轼脑中浮现的都是王安石意气强悍、强盛的情况,岁月消磨了王安石的志气,也好像摧毁了王安石的身体。两人虽然一见没有如故,再见却像老友重逢。苏轼离开金陵到仪真后致信王安石云:“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与王荆公》二)这一刻,苏轼把当年的矛盾放在一边,同是新法受害人,应该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王安石的人格魅力了。王安石劝我在金陵买田退居,但流失的岁月再也追不回来。十年前,也就是熙宁七年(1074)四月,因为王安石一再要求加强宰相的权力,引发了宋神宗的不满而被罢相,随后闲居金陵十个月,那个时候的苏轼还在杭州通判任上,五个月后移知密州。苏轼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后不再重回朝廷,早点寄情山水,则显然可以更多地享受到自在人生的乐趣,而自己如果在杭州通判任满后也跟着王安石一起退隐江湖,则后面的乌台诗案、备受磨难,也就可以避免了。“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苏轼《次韵荆公韵四绝》其二),你也不用刻意变法,我也不用刻意反对,顺应自然才是人生最好的安排。所以“从公已觉十年迟”,是从后来两人的经历回想到人生的选择之难。这个时候的苏轼对人生意义的体会已经非常深刻了。
苏轼在金陵待了大概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并非都是与王安石盘桓在一起。